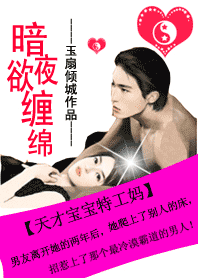零号特工-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湖蓝在卅四要拔步去追前把书塞到了卅四的怀里,并看着那老头脸上由做作的着急变成做作的微笑。
“这孩子,你对人真是太好了。这么点事,就戳这等着?雨衣呢?”卅四转身责怪纯银,“打把伞啊!他年青不懂事,你们要管他呀!”
纯银诚惶诚恐看一眼他杀人不眨眼的上司,湖蓝面无表情,卅四则全心全意扮演着一个只顾琐碎而爱心过剩的老废物。
湖蓝对纯银说:“你走吧。”
纯银如蒙大赦地正要走开,卅四又开始吵吵起来:“这书不对啊!”
纯银站住,这事要出了错他能掉脑袋。湖蓝的忍耐早超过了极限:“哪里不对?”
“好大一股药味。”
“放我身上了,我身上裹了药。”
卅四居然闻了闻湖蓝:“不一个味。”
“别胡搅蛮缠了。这不是密码本,不过你随手抓来的破烂。”湖蓝很想从老头子脸上看出个端倪,但他无法从那张涎脸上看出分毫能把握得住的东西,卅四的脸永远是公开了一切又隐瞒了一切。
“我一直尽量尊重你,因为先生称你为他的对手。现在你让我失望。”
“嘿,别跟小劫学得这套不人不鬼的吧,我常想他训完你们是不是背过身就笑脸。重吗?”
“什么?”
“腿上,那伤。”
“不重。已经锯了。”
卅四惊讶并有点痛惜地看了湖蓝一眼:“你一直是用一条腿站着?”
“两条。”湖蓝用手杖敲了敲自己的腿,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给卅四听,同时他用沉默向卅四展示自己的仇恨。
卅四似乎永远不会接收到湖蓝永远在发送的仇恨,他叹了口气,惋惜道:“这次死伤的人太多了,如果换个阵地,都是对付日本人的好手……这是最可惜的。”
“忙完这事我会去捕杀让我受伤的人,带回他的尸体,这是最好的。”
卅四看了看他,有点想说而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我也不再和你斗了,我一直想让你成了疲兵,可不知道你没了一条腿,我真不想害你这么仇恨和愤怒。”
“你他妈的给我去死!”湖蓝真的是忍到了头,卅四和他斗嘴只让他愤怒,卅四的怜悯和宽容则让他抓狂,最能伤害湖蓝的便是来自他人的同情。
“快去睡吧,孩子。我知道为了不输这口气,你能这样耗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可这真的不重要。”卅四苦笑,并决定让步,“好的,我先去睡。我已经很累了,我比你更累。”
湖蓝瞪着卅四佝偻着离开的背影,他像个无法出拳甚至出拳也会打空的拳击手一样无力:“你这个奸猾的老鬼!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我会相信的!全他妈是假的!连那个狗屎密码本也是假的!”
卅四连走连唠叨:“是的,它是假的。是我随手从家里抄出来的,小时候我拿它给儿子讲故事。”
“还是假的!”
卅四站住,苦笑着,那种苦笑最后成了一声叹息:“我们站在战场上,以为我们是不同戴天的仇敌,刀枪剑戟,彼此相向,早忘了信任是怎么回事。岂不知在日本人眼里看来,这两队人也许只是待收割的麦子。”
“你干吗一心地把话头往鬼子身上引?”
“因为半个中国都被占了,他们现在是最想看到我们自相残杀的人。孩子,去告诉劫谋,所以我这次出来,不想和他作对。”
湖蓝冷笑:“你哪有和先生作对的本钱。”
卅四以微笑对湖蓝的冷笑,那样的微笑总让他的对手觉得煮熟的鸭子要飞。
“是的,我要什么没什么,所以更不会和你作对。”卅四说,“我去睡了。你也早点睡吧,这样子下去,跟除了劫谋的所有人都做敌人,你会被耗惨的。”
湖蓝用一种想发作又不知该不该发作的神情目送卅四走开。
“听够了没有?”
一直窝在旁边不敢出声的纯银被他吓得浑身一抖:“是!”
“去给劫先生发报。”
“怎么说?”
湖蓝一字一顿地道:“目标声称,他没有敌意。”他的表情和腔调都认定了卅四有不可调和的敌意。
36
宿夜的积雨从屋檐上滴下,朝勒门依然躺在泥泞里。
零仍被绑着,他看着雨地里的朝勒门,那早已经是一具被众人远离的可能传染疫病的尸体了。
阿手过来,一只脚踢了零一下:“可以放开你,不过你得保证不靠近那具尸体,不做任何找死的事情。”
“放开我。”
阿手沉默着。
“我保证。”
绳子被解开,零坐了起来,揉着几无知觉的手脚,恨意俨然。他仍然看着外边朝勒门的尸体,但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阿手在他身边蹲下:“我会保住你的。就算这里人都要死,你也是最后一个。”
“也在你的后边吗?”
阿手冷淡地看了看他,又将头转向一直紧闭的大门:“真搞不懂。不过是不让你靠近一个必死无疑的鞑子,也能搞得你这么恨天怨地。”
零同样地冷淡着道:“我也不知道。”他看着了无生气的朝勒门那具已经不可能再喝酒吃肉做恶作剧的躯体,他的眼睛里有悲哀,也有丝许残存的欢乐。那具尸体将放到下午才会拖出去。
门上的锁钮在动,对着院里的机枪也抬了起来,对准了院里摆出一个弹压的架势。一个猥琐的中国男人进来,看样子是个保长甲长一类的,后边是一群更猥琐的日本兵。
日军拿着一根很长的绳子,那名中国男人指到谁就在谁腰上打个死结,他们很快就这样串了四五个人。
阿手低声说:“别被他指到,最好别被他看见。你我都不该死在这么条走狗手里的。”
但是那保长已经转身看着他们,并且径直向这边走了过来。阿手木然地看着,零像他一样木然,阿手的两名手下一个挡在阿手身前,一个脸色惨白地推开。保长只看着阿手,冷笑:“湖蓝让我告诉你,你来错了地方,应该就在三不管扫地擦桌子的。他说你菜做得不错,如果能活着出去,可以伺候他。”阿手的眼里在冒火,但只是低下头,然后他打算站起来,做绳串上的最后一个。保长摁住了阿手:“急什么。湖蓝说,慢慢来。”然后他的手指从阿手肩上抬起,指着刚才曾经挡在阿手身前的那个中统:“你。”被指的那人怔了一下。阿手的眼里也黯然了一下,仍然坐着,没有表情。手下全无反抗地从阿手的身侧走到了身前,向阿手点了点头,那算告别。
“你是我最好的手下,阿忠。”
“站长再见。”阿忠看看他的同伴,“再见。”
那行人悄无声息地出去了,门再次关上。
阿手漠然地坐着。零也漠然地坐着。
另一名中统骂了起来:“妈的,他说再见是什么意思。”
阿手忽然跳了起来,狂暴地对那中统一通拳打脚踢,然后一屁股坐在零的旁边。
一个被囚禁者在昨夜积下的水坑喝水,然后悄无声息地倒下。没人靠近他,也没人躲开他,死亡在这里已经微不足道了。
零站了起来。
“别费力了。进来这里的人活不过一个星期的,因为鬼子从来不管饭。”阿手瞪着零,看看刚刚从零身上解下不久的那根绳子。
“那你还何苦对我倍加呵护。”零苦笑,蹲下。
这种嘲讽现在只能让阿手不屑地咧咧嘴:“我不想装相,只是肚子饿,就尽量省些你费在斗嘴上的力气。你不饿?”
“挨饿是我的人生,什么是你的人生?”
阿手看起来有些愠怒,但眼神里却带了点笑意:“共党,你在讥讽还是玩笑?”
“伸手给自己挠痒而已,你觉得我要掏枪杀人?就因为站了不同阵营?”
“明白了。你继续吧。”
“继续什么?”
“就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挖苦军统,拿中统逗个乐子,或者你真那么放得开,说说你们共党的笑话。我虽然愚钝,可也知道你在和我配合,你也想活下去,这是上鬼门关的路,忘忘忧才能活得下去。”
“被你说穿我倒怯场了。”
阿手眼里的笑意更浓了。
零再度起身,捶打着墙根,找准了某个点,然后他走向那个水坑。
阿手又严厉起来:“你一定要害死你自己吗?那个人已经死了,那水有病菌的。”
“我需要水。”
“喝屋顶上滴下来的。”
“不够用。”
阿手没再阻拦,那也算一种信任。
零脱下衣服浸在水洼里,直到那衣服湿透,回身,把湿衣服上的水浸在屋角的墙根,用一块捡来的石子开始掏挖。
阿手不抱希望地看着。
“借贵方吹毛断发的宝刃用一下。”零的手伸向阿手。
“要不要告诉你这鬼地方的墙有多厚?”
“很厚。要不也不会拿它当监狱。”
“你还是坐这跟我说说笑话吧,这辈子没想过还能跟共党说笑。”
“只希望出去以后你我还能这么说笑。”零的手仍然近乎蛮横地伸着。
阿手看着那只手,苦笑:“给他。”没有回应,阿手有些责怪地看他仅存的那名手下。那人正蜷在墙角哭泣。阿手愣了一会儿,过去,他没说什么,把那块他们磨制的锈铁片从手下身上掏出来扔给零。然后重重给了手下一脚:“哭就是放弃。”手下身子震了一下,啜泣变成了压抑的哽咽。
零走开,又去掏那个全无希望的墙角。
阿手又给了手下一脚,但这一脚轻得多了。
零在掘墙根处渐渐掘出了能放下一个烟盒那么大的坑。囚徒们在身后或坐或憩,没人关心,零也不用避讳他人,长了眼睛的一看就知道那是徒劳。
阿手终于绝望地从零那厢转开了视线,他手上一直在抛着一块石头。手下仍在那里哽咽。阿手把石头摔了过去,砸得手下的额角见了红:“你也差不多哭够了,在共党面前不要太丢面子。”
“站长,鬼子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阿手他阴沉地冷笑着,“湖蓝要我们死,可不要我们向鬼子泄露机密,在他的心思里,这就不叫汉奸。”
“我们会被当做黑市、当做走私贩子、当做青红帮袍哥会这些下九流的杀掉,像狗一样死。”
“我们什么时候又成了上九流的呢?”
“这么死不值当。”
“你想说什么?”
“我们可以不像老六和阿忠那样死的,我们知道很多秘密……”
“不行!”阿手看一眼墙头上的日军岗哨,压低了声音,“绝对不行。很多人说我们是汉奸,可我们是特工,绝对绝对不是汉奸。”
“可是……”
“可是绝对不要让我失望。我知道你不是怕死,只是不想这样死。”
“是。”手下的回答只是在自我挣扎,像是回声。
37
军统的据点门外停着一个小小的车队,湖蓝的车正在准备出发,整个车队看起来形同某个富家公子的出行。
湖蓝已经醒了,还没有全副披挂,他笔挺地坐着,精神抖擞但是内在却充满挥之不去的沮丧。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断腿,眼里满是血丝,昨晚他没有睡好,正像卅四说的,他是靠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撑到现在的。
纯银进来。
湖蓝问:“准备好了?”
“好了。”纯银回答,随即一纸电文递了上来,“先生回电。”
湖蓝有点茫然:“回电,回什么电?”
“昨晚给先生发送的电文:目标声称,他没有敌意。”
“哦。念吧。”
“愚蠢。共党的存在就是敌意。”
湖蓝诧异地看了看纯银:“什么意思?”
“就是先生说你愚蠢,共党只要还活着就是对我们的威胁,不管他有没有敌意。就这样。”
“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