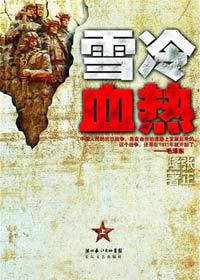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露营之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四溅,烧人烧衣服。锯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觉的地场。把雪尽量清除,底下一层摆好,上面一层十字交叉放着,再一层也一样。一人来粗的木头,每层4根,摆放3层,能烧一夜。木头细了,就得加量。
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