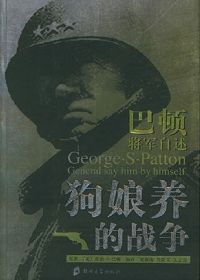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晚上,我没有一点瞌睡。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24) 八五年七月三日,小雨。
不下雨的日子有好几天了,眼看着洞里的水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坠落的过程显得非常的懒散,完全失去了雨量充足时,水滴坠落时的完美风采。因此显得非常的讨厌,我已经醒了有一会了,听到了雨打芭蕉叶的噼哩叭哒的声音,我懒得睁开眼睛,我太清楚下雨是个什么样子了,雨滴从芭蕉叶上不停地滚落下来。在以往,总是让我联想到妈妈身上流落的汗水,可在今天,我想到的却是妈妈的泪水,妈妈可能知道我在随时随地的面对死亡,却一定不知道她的儿子每时每刻都在炼狱一般的苦熬着。她要是知道了,泪水肯定比外面芭蕉叶上的泪水还要多。
雨可能是在下半夜开始下的,我听到洞内的水滴变得急促了起来,想必坠落的过程也完美了起来,我懒懒地半睁眼睛,只是想验证一下水滴是否完美地坠落,并不想去认真地欣赏。光线非常地阴暗,我索性从铺上坐了起来,头在弧形钢板上磕了一下,我把脖子放松,免得再次磕到头,伸出手指去点击即将坠落的水珠,水顺着手指流了下来,我不停地点击着,试图抢在所有的水滴滴落之前去点击,最终我的手指点不过来,水滴多而且形成的快,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点,津津有味地点了起来。
郝爱来了,他问我玩的过不过瘾,我非常肯定地说过瘾的很,他也点了起来,我告诉他,说在水珠即将滴落前去点是最过瘾的,由于他的心没有完全地静下来,在点击的时机上没有我把握的好,他停下来告诉我,叫我回去参加43号阵地的防御,这里由别人接替。
郝爱说完就走了,我除了战斗装具外,没有什么要带走的东西,他知道我要离开了,和原来一样,他什么话也没有,从他的脸上更看不到他是怎么想的,我默默地收拾着战斗装具,很希望他能说点什么,虽然我不喜欢他的自闭和古怪,虽然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可他依然是我心理上最值得依靠的人,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不,应该说是朝夕相守,一个多月的生生死死,早已让我们没有了距离,无需真正的交流,却已将生命托付给了对方.我更知道,如果我们有谁先负了伤,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救护对方。
我一边整理一边想着这些,他似乎也想为我做点什么,把我枪上的一块泥土擦掉了,我由衷地谢了他,实在没有什么留给他做纪念的东西,只有一件我穿过的背心,他极力地推辞,看我是真心的,他也就收下了。
接替我的人很快就来了,我也一切准备就绪,最后看了一眼我钻了一个多月的洞,紧紧地跟他握手,互相说着"保重",松开手的时候,我在心里祈祷这个古怪的家伙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家和他的亲人团聚。
从40号到43号很近,只用了几分钟就回到了43号阵地,班长把我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猫耳洞里,其实洞是完好的,只是因为正上方是高机掩体,大量的雨水才能渗入地下,这个洞挖了三米长,大量的水滴居然滴水成河了,一股股细流从洞中流了出来.洞中散发着难闻的朽木和发霉的味道,班长帮我找来了尼龙雨布,把雨布用电话线套在洞的内面,上面的水滴就顺着雨布流向了两边,再用工兵揪铲除洞内的烂泥,铺上弹药箱,水流从弹药箱下流过,不到两个小时,"家"就这样安置好了。
正当我躺在弹药箱上享受"家"的安逸和温馨时,班长给我送来了"光荣"弹,一颗非常精致小巧的手雷,手雷全身漆黑,拉环拉火后0到2秒就爆炸,严格意义上说,手雷不是进攻武器,而是地地道道的自杀工具,在战前,我们就接受了宁死不当俘虏的教育,如果在战斗中弹尽粮绝或是已经无力反抗,那么这颗手雷就是留给我们自已的。
把手雷拿在手里,我认真地看了看它的构造,其实和手榴弹差不多,要拧开保险盖拉出拉环才能爆炸,手榴弹预留了空中飞行的时间而手雷没有,如果因伤而不能拧开手雷的保险盖呢?我觉得手雷作为自杀工具,在设计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25) 八五年七月四日,阴有小雨。
40号阵地是一个半环形阵地,而43号则是一个独立的环形阵地,与40号成钳形状的方向,坡度不是很大;正面就是越军的黄泥坝防御阵地,通往42号的交通壕;在钳形状顶端的外侧处开始向下延伸,这条交通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越军反扑最紧张的时候,我和陈成利就是从这条交通壕里,将两名无线电通信兵送到了最危险的41和42号阵地,整个的护送过程对我和陈成利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再过来就是二营机枪连一班长的哨位,班长是江苏人,和他一起值守这个哨位的是来自湖北钟祥的刘国清,我回到43号,最高兴就是刘国清了。我和他同一年入伍,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他虽来自钟祥,我来自京山,但都是湖北人,老乡的概念让我们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亲近。而他又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也很喜欢和他一起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神侃。
从一班长的哨位开始,40度到50度左右的坡度突然刀削斧劈一般地成了80度左右的陡坡,虽然有一些树,而且坡高有二百多米,一般情况下视线还算清楚,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算是一处";天险";了。这处天险一直延伸到刘军医他们住的大洞,我和陈成利送通信兵去42号阵地就是从这个大洞里出发的,这个洞处在和40号阵地结合部的位置上。
";天险";的宽度也就三十米的样子,我的猫耳洞就在这个位置上,距离一班长的洞只有六七米的样子,位置已和越军阵地形成了背面,如果不是炮弹直接命中洞顶,应该说,在这个洞里还是很安全的。而我这个洞不同于其它的洞,整个洞体的高度是高于战壕的底平面的,因此没有配套的站岗的地方,我问班长,班长也未置可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这个洞的岗是站也可以,不站也可以的。为此我非常的开心,再也不用去熬那漫漫无边的长夜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郝爱今天才从40号回到43号,他来自胶东半岛的栖霞县,红通通的脸庞透着纯朴和坦诚,为人很大度,从不计较得失,他特有的胶东口音,本身听起来就是一种享受,他长得虽然不帅,但跟他在一起,你的心里总会有一些愉快的感受。我很喜欢和他这样的人相处,昨晚虽然在很";安全";的洞里睡了一夜,但洞口没人站岗,一个人睡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他的到来,让我更开心了,想着两个人一起睡,心里不知道坦然了多少倍。
双方的炮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是一个齐射,更多的时候是单发的冷炮袭击,突然就有一发炮弹打到阵地上,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上午42号就有一人被炸从43号抬了下去,而这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谁负伤已经不是新闻,除非亲眼看到了,否则不会往心里去,负伤的新闻没人讲,更没人听了。如果有谁不识趣硬要讲的话,听的人顶多关注一下伤到了什么地方,是哪里人,仅此而已。
或许大家都和我一样,大家都已把生死看淡。。。。。。。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26) 八五年七月五日,晴转小雨。
昨晚天一黑,我和郝爱就钻到洞里躺下了,郝爱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也有米的样子,我们两个大个子挤在窄窄的用弹药箱搭成的铺上,直能直挺挺地躺着,感觉很不舒服。在早上醒来时,郝爱的一条腿很舒服地放在我的身上,看他的样子,好像睡的还不错。
我起身钻到洞外,伸了个懒腰,感觉特别地舒服。其它的阵地上偶有枪炮声传来,而43号则显得很安静,我走到刘国清的哨位上,他的怀里抱着冲锋枪,闭着眼睛很安然地半躺在哨位上。我随手捡起一根细小的杂草,轻轻地撩拔着他的眼睛,他懒懒地半睁着眼睛叫我别闹。我看他还想睡,有些无聊地回到了我自已的洞口。
郝爱从洞里钻了出来,也痛痛快快地伸了个懒腰。我们会心地一笑,不站岗的夜晚,感觉确实不错。而看到站岗的人因熬不过漫漫长夜而打瞌睡时,就连阵地上的指挥员都不会因此而去批评谁。因为打瞌睡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和克服的事实,谁都知道打瞌睡会有生命危险,可是长达五个小时的静坐却是谁都无法克服的。
我提议和郝爱来一次打树枝比赛,郝爱欣然同意,他的枪上沾满了泥土,显然是没有很好地保养过。果然,他的枪机拉不开了。他用力地拉着,却怎么也拉不开,我得意地告诉他打一枪就行了。这个问题我曾遇到过,是射击后没有擦枪造成的硝烟沾连。
郝爱对着树上干脆来了一梭子,把一弹匣的子弹全打了出去,我也对着树干打了起来,忘记了比赛的事情,他的枪机又活动自如了。不过,他如果这次不擦的话,时间长了还会粘连上的。
郝爱开始擦他的冲锋枪,我认真地打着树枝。他一边擦枪,一边评论着我的枪法。
在阵地上,白天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没有了按时吃饭的习惯。下半夜不站岗的,如果没有其它的任务,睡到什么时间都可以。每个人都配发了足够的压缩饼干,还有定量配发的各种各样的罐头,而多数的罐头我都是上了阵地后第一次吃到。牛肉我是不吃的,五天一斤的牛肉罐头,我已经有好几斤了。早餐我送了一瓶给郝爱,其余的我都和别人换成了桔子罐头。
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班长来问我们去不去34号阵地看病。说34号阵地上来了几名女护士,专门给我们送医治皮肤病的药来了,有病的可以轮流去看。其实皮肤病就是烂裆,开始我和郝爱一听是女护士,心想没病也要去看看的。从五月二十五日上前线到现在,就没看到过一个女人的影子,当听明白是看烂裆病时,我几乎是和郝爱同时抢着说不去,又同时埋怨为什么不派男医生上来。
班长统计了烂裆的人数,几乎所有的人都烂了裆,而所有的人又都相互隐瞒着,唯恐别人知道了会嘲笑自已,其实每个人又都在默默承受着烂裆痛苦的折磨。
班长问我愿不愿意去34号领药,我笑说这样的好机会应该是班长的,其实我很想去,但我害怕护士们会查看我的症状,更害怕是以一个烂裆病人的形象出现在女护士面前。
班长很快就回来了,二机连的一班长笑问护士是不是很漂亮,班长连声地说漂亮,说看一眼就能让人舒服一个星期。一班长则调侃着班长说:“在这样的环境里看一眼,应该是舒服一个月才对”。
出呼我们的意料,班长带回了很多的信,这是我们最盼望的一刻。他走到我们的洞口,手里举着信,高喊着我和郝爱的名字,我和郝爱兴奋地冲了出来,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信,把郝爱的递给郝爱,我的只有两封。一封是弟弟代表父母写来的,一封是姐姐写来的。看到信封上熟悉的故乡名称,看到弟弟和姐姐熟悉的字迹,一股巨大的暖流涌上心头,整个的身心被亲情温暖着。家乡的穷山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