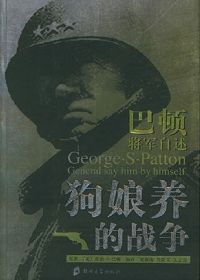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供应了)。还大量供应各类罐头,有红烧猪肉,午餐肉,牛肉,回锅肉,炒兰丝,炒素什锦。水果罐头有桔子,波萝,黄桃和犁子。另外还有大量的新鲜水果供应(也是没有的事)。
至于我们怎样作战,由于我们是阵地防御,敌人攻,我们就依托坚固工事抵抗,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人可抗敌一个班的进攻。主要是因为我们弹药充足,工事坚固,还有各种火炮的支援。防范精力主要放在晚上,白天都休息。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岗,吃饭,睡觉这三大项,是非常轻松的。
至于什么时间从前线撤离,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据上级透露,我们在前沿可能还需要呆一些日子,撤离后会在云南休整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山东。
尊敬的***同志的父母!我作为他的战友,对您们的家庭关心的很少,感到非常惭愧,这次来信,也许能弥补一些,您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我向上级反映,上级是会向您们的当地政府联系解决的。
祝您们二位老人幸福安康!
此致! 梁吉发
1985年11月27日。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80) 八五年十二月二日,阴有雾。
清晨七点,我正准备对《心灵的邮路》进行修改,刚把草稿看了一遍,忽然听到远处万炮齐鸣,我军的加农炮,榴弹炮,火箭炮,其中还夹杂着迫击炮的声音,一齐对那拉口方向的越军阵地开始了齐射。随后猛烈而又持续不断的爆炸,透过浓雾的水分子,从那拉口方向传来,就像是在十分神秘的空间里演奏着火炮交响曲。乐谱很长,演奏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才告结束。
如此高密度的炮击,我们都猜测是兄弟部队对越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就有消息传来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是199师趁敌换防立足未稳之际,对敌进行拔点作战。
从声音上听,越军也在对我攻击部队猛烈炮击,把火炮交响曲的演奏变得更为恢宏壮观,甚至是惨烈。
我在心里推测着战事的进展。此时此刻,我知道战友们正在流血,正在牺牲,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正在失去他们的儿子,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正在失去他们的亲人。
从炮击的频率和密度来判断,战斗进行的很激烈,让人不敢想像,在如此密集的炮火履盖下,一个士兵能够平安地走出战场,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此生命就显得尤为脆弱和不堪,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犹如微风吹动草灰一样的容易。
我知道,从我们走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它属于国家,属于军队。在慷慨激昂的战斗动员中,很多人都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表达了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所有的人都悄悄地写好了遗书,并把遗书装进写好了地址的信封里,既便牺牲,遗书也能准确无误地寄到父母的手里。
几乎所有的遗书都在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愧对父母,愧对兄弟姐妹,愧对所有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亲人!
每一封遗书都能催人泪下。
没上前线的时候,常常从报纸上看到类似的报道,我总是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记者们故意的夸大和宣传,是报道和新闻的需要。特别是咬破手指写血书的场景,对此更是嗤之以鼻,总认为那是做给人看的;有很大的做秀的成份。而现在再来感受这样的场景,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慷慨激昂,什么才叫做热血沸腾,什么才叫做慷慨赴死。
今天的战斗之后,将有很多的遗书被寄送到亲人们的手上,撕心裂肺的疼,将长久地撕扯着烈士父母和亲人们的心。
火炮交响曲纵然壮阔而惨烈,终因浓雾不能透视而失去了对它的兴趣,而潜心专注于《心灵的邮路》的修改。
一直到下午四点半,炮击才完全停了下来,随既就有消息在阵地上传开,我军攻克越军两个阵地,全歼守敌七十余人,我军一个主攻排全部阵亡,幸存者仅有一人,预备队也有较大作亡。
我牺牲的战友们,你们一路走好!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81……128) 八五年十二月五日,阴有雾。
每次的攻击作战之后,前线总会出现一个相对的平静期。
这次也不例外,双方似乎在二号的大战中打光了所有的炮弹,所以这些天里一发冷炮都没有打过,只是偶尔能听到附近阵地上的枪响,而这白天的相对于听惯了枪声的我们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解闷的行为。
由于战场的暂时平静,而降低了死神对生命的威胁,继而对父母的思念也淡忘了一层,生活略微正常了下来。
但在这样的环境,那有什么持久的正常可言,干扰不是来自越军,就是来自气候和家庭。因昨晚下半夜是我的岗,阵地上是出奇地静,但越是宁静,哨位上的我就越是没有丝毫的睡意,越是宁静,就越容易产生思念的情结。我想喻红,但想的更多的是父母。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十七岁半)就离开了他们,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我真的好想他们。
思念总是那样的伤感,我本不想过多地思念,可情感总是那样的脆弱,一不经意就拔动了这根情弦,让你充分体会到思念的温馨和甜蜜。
清晨七点的样子,陈成利醒了,他把洞里唯一能躺下一个人的铺位让给了我。阵地不存在了,自己也不存在了。从钻进洞里躺下到睁开眼睛,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但伸手看表时,已是上午的十一点了。
是负责后勤的李久清叫醒的我,我没想到他能上来,他是专程来看我的。从上了前沿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见面了,我和他同时分到炊事班,同时都有连队用人不善的感概。不同的是他认真地工作,我却能不干就不干,能马虎就马虎,甚至还要跟带我的李茂友打架。我和他是老乡,行事风格和观念的不同,让我们常常爆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每次都是争得面红耳赤后气得摔门而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过不了一天,我们又都忍不住走到一起,和好如初。慢慢地我和他成了最知己的战友。
他的到来让我异常兴奋,他说要在这里吃饭,不巧的是一点菜也没有,连罐头也没有了,只好让他吃了一碗有点稀的米饭。好在他知道阵地上的苦,吃什么他并不介意。
他带来了两封信,一封是父亲的,一封是弟弟的。父亲识字,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他在信里充满了对我安全的担扰,同时也给我提出了希望。弟弟则在信里寄来了一张母亲的病情诊断书,说母亲十分地思念我,让我十分震惊。我虽不懂那些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年近六十的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思子心切,真的让人很担心。
如果是在内地,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回去探望的,可现在是在前线,妈妈原谅我吧!您哺育了我,我则在十七岁就远离了您,而且在您身边的时候,由于不懂事又常常惹您生气,现在懂了,却又不能照顾您,在您的心里,或许还保留着那个不懂事的儿子的印象。
妈妈!我真的是变好了,我真的是懂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珍贵,我知道了母爱的伟大,我知道了您和父亲的艰辛!我现在很努力,我一直在坚持自学,我渴望成才,渴望立功,更渴望成为英雄!我正在用您给与的五尺之躯战斗在祖国的最前沿,我希望这能够带给您无尚的光荣和骄傲。我知道您担着心!父亲打过仗,清楚死神总是和我们咫尺相随的,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让我们母子天上人间两分离!可是妈妈!您年迈体弱,疾病缠身,且又终日在思念和担扰中渡过,我也担心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见不到您呀!
妈妈!亲爱的妈妈!为了您的身体,也为了我们母子能够相见,我垦求您不要担扰,不要牵挂。您忘了我吧,忘了您这个在前线的儿子!
我边看诊断书边想着这些,竟然当着李久清的面泪流满面,他没有安慰我,他知道安慰是多余的。他却给我讲他的母亲,讲他母亲对他的教诲和期望,讲自己曲折的经历,感情。
在他的讲述中我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他描绘中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多么地相像啊!坚韧,勤劳,善良;自强。我想,这大概是天下母亲共同的特征吧。
李久清把我的津贴费也带了上来,钱在阵地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知道父母的艰辛和贫困,我写好地址,委托李久清一分不留地寄走了,也把我的祈愿和希望寄给了妈妈,祈愿妈妈康复,祈愿妈妈长寿!祈愿我们母子能够相见!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82) 八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阴雨雾。
老山战区严格意义上属于亚热带地区,它没有春夏秋冬的区隔,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现在应该进入了旱季,可多雨多雾的天气总让我们觉得雨季还在继续着,让我体会不到旱季的模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有太阳的时候,穿件背心都觉得热,而在雨雾交加的日子里,穿两件衣服都感到寒冷。
李忠彬穿上了大衣,他可能听说了上面下雨的日子是有点冷的,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件大衣带了上来,他跟宋振清一样,在医院里养好了伤,也养得白白胖胖地上来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你来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的全部是布鞋。”
问他是哪里寄来的,他说没看清,我感到很疑惑,家里刚来过信,并未提及此事,也许他看错了分队。巧得很,一连有个干部与我同名同姓,上次我的一封信就是他收到了,而我也收到过他的信。因李忠彬没看清地址,邮包可能不是我的。
今天是副班长苑庆敏的二十三岁生日。他是个勤快人,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都给我们做饭,不做饭时;就不停地鼓捣他的猫耳洞,直到他的洞在32号阵地上是功能最齐备的洞后,他才罢了手。
为了给他过个像样的生日,酒是一定不能少的。借着刘昌贵和宋振清下山背粮的机会,我请刘昌贵弄了四瓶啤酒上来,四瓶啤酒的重量不轻,加上粮食的重量,爬天梯就会更加困难。
看到刘昌贵大汗淋漓地卸下身上的粮食和酒,我的心里颇觉过意不去,特别是酒钱也是刘昌贵垫付的。因我的津贴费全部托李久清寄给了母亲治病。为了给战友过个像样的生日,我这是第一次负债。
宋振清对此十分不屑,他虽没有说什么,但我读懂了他轻视的眼神,他可能认为我在巴结和讨好副班长。
“生日宴”没在一起举行,分成了两拨人马,一拨两瓶啤酒,半锅土豆。一拨人吃,另一拨人则留在哨位上观察,因为今天雾大。
土豆的味道不错,可能是有啤酒的原因吧。可宋振清的眼神让我始终不能释怀,苑庆敏既兴用口琴吹了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的心里依然有阴影残留着。
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李久清打来了电话,我这才确认,我真的来了个大邮包,请示了梁吉发,我立马飞奔去取。
途中遇到了老大哥刘医生,他说实习期满就要离开了,用他随身的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相;用着留念。
老大哥是个很好的人,耿直豪爽而且热心。刚才我都走过去了,感觉是他,我又回过头来叫的他,换成是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