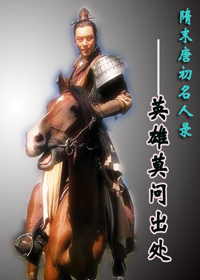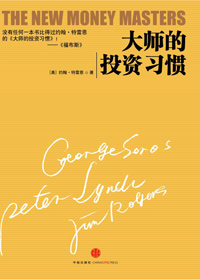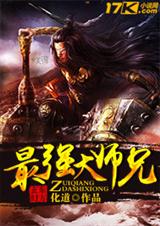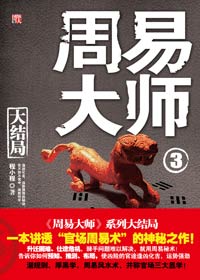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黄宗江
1
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尽管如此,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燕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时在学校里的我们并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燕京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并不传教,也没有说基督教教义就是真理。学校里有一些团契活动,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司徒雷登在创办和执掌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实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校训的。后来在批判燕京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说燕京校训中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服务是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应该追求可以得到自由的真理,当每个人都能拥有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时,一个自由社会就来临了。我们为了什么服务,就是为了能够追求真理以服务。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
2
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1937年我在耀华中学面临毕业,我本来是想到南京报考国立剧专,但是南京沦陷了,没有去成。当时的国立大学都南迁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一个是辅仁,一个是燕京,都是教会学校。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两百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七百多人。据说司徒雷登到过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拜托他对沦陷区的学生加以照顾。当时北京还叫北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学管北京还叫北平。在这种小小的称呼之别上,其实含着很复杂的关系,这就说,燕京大学根本就不承认日本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学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2)
3
我认识的燕京人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的,他当年是燕京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作为西语系的学生,黄宗江对于这个名字当然更加熟悉。甚至对于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国东部小城绮色佳,黄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别的情愫,这为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爱屋及乌”又增加了一个注脚。在黄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黄宗江这样描述那个美国东部小城:
……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
在那篇文章中,黄宗江写到了谢迪克:
1938年秋季,我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图片009
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4
在不同的叙述中,黄宗江两次说到了离开未名湖。离开未名湖或许是黄宗江的一个心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决定离开燕京。当时快大考了,我也有点怕大考。我找到文学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周院长说:“你先冷静冷静,咱们再谈一回。”由于演剧,加上我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我在燕京还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吗?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离开校园,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经有了抗日问题。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说:“这个……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说到了内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学生。我又说:“我跟他在艺术流派上不是一个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曹禺、张骏祥他们。我向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我关心的感谢,就离开了燕京大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学上我的第九年大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毕业。”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黄宗江没有说,或许他认为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解放前夕,黄宗洛就到解放区去了。”对于自己三弟当时的情况,他也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了。不过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5
命运再一次把黄宗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黄宗江在许多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红卫兵在我家抄家的时候,抄出了一大堆照片。照片哗啦撒在地上,出乎我的意料,里面有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我马上把脚踩在上面,企图销毁罪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其实照片的事情很简单:当时学校门口有卖明信片的,燕京风景一套六张、校长照片一套六张等等,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嘛,就买了。后来我海走南北地流浪四方,就把旧照片存放在姐姐家里。姐姐把这些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翻这些照片。就这么一直放着了。这下子我成了“司徒雷登的黑宠儿”,当时我在学校里又演戏又闹自杀,虽然也很名气,但是要说到“司徒雷登的黑宠儿”,我还算不上。
虽然因为母校吃了苦头,但是对于燕京的感情却日益见深。每年的4月23日,燕京的老校友都会在燕园重新聚首,在那个时候,黄宗江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
2004年校友聚会的时候,北大校长说:“我们一定要把燕京交给我们的校园保护好。”北大校方在公开场合承认北大和燕京之间的继承性,这是第一次。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在讲话中赞美了北大校长对于燕京和北大之间继承性的肯定。
这种赞美,大概代表了燕京人的一种心情。
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所引均为黄宗江口述。
《洋嫂子&洋妹子etc》。黄宗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1月第一版。
《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燕京研究院编。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1)
萧乾,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10年生于北京,1935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入《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6年,萧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萧乾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萧乾还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大事,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文学创作上,萧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与沈从文等人被归为“京派”作家的代表。萧乾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报告文学《人生采访》,及译作《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晚年,他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1999年,萧乾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剑三]基三传之大师快拉脱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