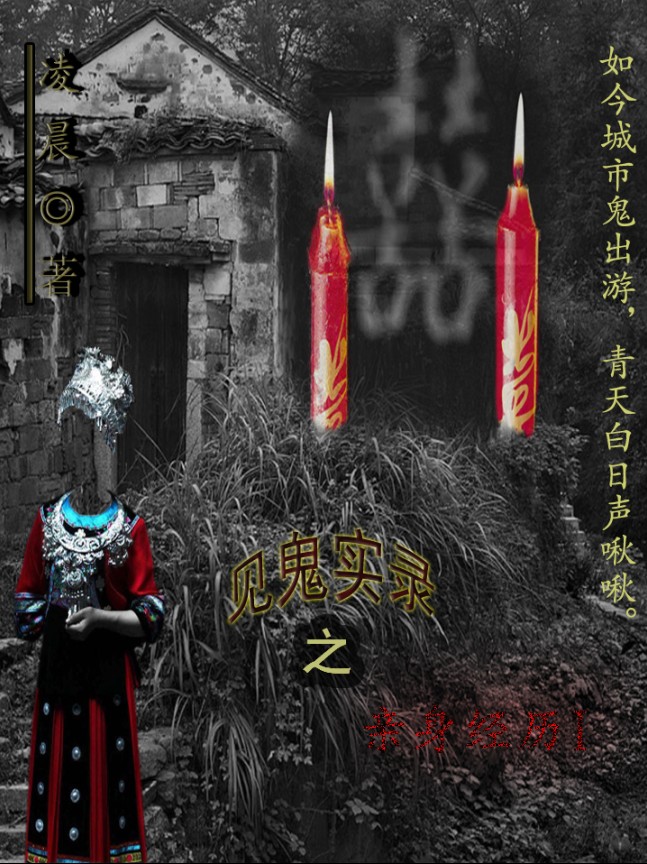尸匠秘情录之喜神会 林佩-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人当场克制不住而流下口水,有人嘴里喃喃喊着妖孽,而排在後头的观赛者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远远瞧见以季堂为首的三个人竟都莫名其妙停下脚步,鼓噪的喊声几乎冲破云霄。
维持秩序的考官查觉有异,直接过来干预了。
「猗傩派自重,勿干扰赛事进行。」
「大师兄你太不小心了!」有人赶紧出来打圆场,是小师弟,他一见到大师兄故意弹开面具,心下了然,立刻捡回面具递给大师兄。
大师兄对考官耸耸肩,「意外而已,别大惊小怪。」
自在从容戴回面具,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头也不回就拉着小师弟走了,反正目的已经达到,老三只要不再出错,肯定能晋级。
曲家人跟柳溪派弟子回过神来,却发现猗傩派弟子已经驱赶自家的喜神上了坡,原来刚刚老三一看到现场,立即知道怎么回事,不就大师兄又耍阴了吗?趁此机会他领着喜神快步通过原本领先的三人,早一步来到坡边,趁搔动时,一举把喜神赶上坡。
被人抢先一步,柳溪派可紧张了,一等自家喜神靠近上坡路段,便曲指往喜神膝盖附近的穴位击打,原本曲膝范围有限度、无法跨跃一定高度的喜神,居然大范围的曲了膝,学普通人一样的上了坡。
接着轮到伶伦曲家,他使用以曲音催动喜神跳舞的方式,让僵直的四肢伸展开来,因此也顺利上了坡。
坡下季堂依旧浑浑噩噩,他看来就像自己所赶的喜神一样,忘了身分、忘了名字、忘了自己站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呆呆注视猗傩派掌门师兄离去的背影,完全不知今夕何夕。
十二。何不泯恩仇
第二轮的赛局里,猗傩派得掌门师兄之助,第一个抵达了终点;柳溪派弟子稳当推进,跟着到达;伶伦曲家运气差了些,喜神随乐曲跳得太高兴,在过坡之後的崎岖石头路段里摔了跤,偏偏那个地方画山羊不容易,曲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山门的季堂从容穿越过他,成了第三名。
季堂虽然运气好,人却不太高兴,他一张脸死沉死沉,像有谁刚把他家祖宗十八代的遗体都从墓里拖出来打了一顿。
至于他在场中的失常表现,恩师自然是把他叫到跟前关心了一阵,他没多说什么,其他师兄弟却是大大哄闹了一阵。
「外头都传猗傩派的人故意使坏,为了扰乱赛者,故意拨掉面具,让师兄分心。」章小恺抢着说。
「不受外界任何的变化而维持定力,是赶尸人最基本的能力,只是……」师父毕竟熟谙人世,意有所指的问季堂,「会让你分心,难道你认识猗傩派掌门?」
「不认识。」为了强调,季堂重复了一次,「徒儿不认识他。」
如此用力的否定,反倒更让人起疑窦,师父改以眼神询问章小恺,毕竟他跟着季堂学习,几乎都在一起,季堂有任何不寻常的心事,章小恺不可能不知。
章小恺还真的不知,猗傩派掌门人的面具掉地时,他被人群给挤开了,好不容易跟上师兄时,已经是後者到达终点的时候。
其他几个刚好有瞄到猗傩派掌门人的弟子这时候开启了话匣子,一个说猗傩派果然如传说中的,专找娘娘腔的家伙入门;又有人批评对方不够汉子,丢赶尸匠的脸,还不如去唱花旦;但也有人小小声说,唉将来若能娶到同样漂亮的婆娘,此生无憾啦……
季堂提早跟师父告退,为了明天的比赛,他必须养精蓄锐,章小恺不放心,说要找些补品给师兄。
季堂不置可否,带着负屈往後头他休息的洞室去了,负屈就是他新养尸婢的名字。
猗傩派人据以休息的山洞里,有师兄弟频频抱怨,说掌门师兄不厚道,居然让祸国殃民的一张脸现了世,这下可好,山洞外头一直有其他赶尸匠来来回回,经过时都故意往洞里头瞄一眼,用意可想而知。
只排两个师兄弟守着洞口根本不够,他们不得不多编派两个守门人,大家都被逼着减少睡眠,轮着去洞门站岗。
掌门师兄却完全没有罪恶感,相反的,他还很得意咧。
「要不是我急中生智,老三能过今天这关?兵不厌诈你们懂不懂?外头人骂的都是我,不是你们,当掌门容易吗我?」
小师弟忿忿抱怨:「现在他们都说猗傩派的人是狐狸精,谁狐狸精啦?他们才是狐狸精,他们全家都狐狸精!」
掌门师兄笑嘻嘻听着,伸伸懒腰说要去洗浴,可能会洗很久,不用来找他,还把二师兄的含冤给借了去,说边泡水边听小曲儿,才是人间至乐。
小师弟不懂,问二师兄,「为什么大师兄要洗很久?」
「因为他是狐狸精。」二师兄说。
小师弟还是不懂啊不懂,为什么二师兄说的话总是莫测高深?。偶尔说点简单的人话不行吗?
猗傩派掌门师兄手执火烛,换戴了另一副面具出山洞,另外有含冤紧紧跟着,那些在洞外徘徊的无聊者,见那不是猗傩派掌门人的面具,加上含冤身上的怨气太重,大多人一见就避而远之,也没人敢拦下他来。
走了约半个时辰,远离所有参与喜神会门派所栖居的山洞群,他钻入另一个小小的山洞中。
落星山中到处都是溶洞、地下河,许多山洞彼此以隧道连接,里头奇岩林立,洞穴忽宽忽窄,彼此连接,宛如迷宫一样,有这么样的一个小洞并不稀奇。
一开始这洞穴窄窄的只够容一人通过,百步之後洞穴渐宽,一处水潭出现。
这水潭原来落在一处竖井口的正下方,瀑水丁泠而下,两三种鱼类及虾在水里头生活。
掌门师兄本就爱洁净,出门在外,得先找好不受人打扰的沐浴之处,这里就是他早几日命令门里所有师弟,探勘出来的好地方。
「含冤,帮我顾着,别让闲杂人进来。」
基本上,掌门师兄早已经把老二的尸婢当成自家物在使唤了。
含冤嘤咛一声,表面含怨,内心狂喜,她喜欢看美男子,更喜欢看美男子洗澡,自从主子带她回到猗傩派之後,她的内心天天都有小花开灿烂,因为猗傩派里各种俊俏标致都有,唉,她甚至还想,这些人不去唱戏,却天天戴着个面具出门与尸体为伍,真是太暴殄天物了。
掌门师兄将蜡烛搁好,脱了衣服,取下发簪任青丝泻流,烛光映出他如凝脂一般的滑润肤质,他宛如一尾鱼的滑入水中,到瀑布下方去冲淋全身。
水深淹没近腿根处,强劲的水流从头顶盖下,他闭起眼睛,水声掩盖四周一切的动静,他的心情也平静,暂时不需愁烦门派的前途、金钱的用度、喜神会的压力──
水潭表面起了变化,身後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水底似乎有什么大怪鱼正悄悄逼近而来。
掌门师兄恍若未觉,拨拨那被水冲乱的湿发,突然间有人自身後熊抱而来,将他横移到瀑布旁的山壁前抵着,扣住他的双手,心口处也被尖利之物相顶。
「你到底是谁?!」身後男子严厉喝问。
掌门师兄微垂眼,看到心口顶着的物品,说:「别弄坏了这簪子,我很喜欢。」
握着簪子的手一动。
「这是我买给不回的青玉簪。回答我,你到底是谁?!」
掌门师兄一笑,微转头,笑容带动眼角的泪痣,让他整张脸更加的绮丽动人。
「我本姓燕,名归,取字不回,我就是不回。」
「我不相信!」握着青玉簪的手加了几分力道,簪尖又刺入了些许,「我亲自验证过,不回已死,而你确确实实活着,除非听魅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安国君陵墓里,他也说过死者不能复生,起死回生这种事,悖逆天道。」掌门师兄、也就是不回,这么回答。
「所以……」季堂咬牙切齿,一字一字在不回的耳边狠狠问:「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使用了化鬼术。」不回解释,「我们猗傩派的秘技有释阴一术,能隐藏体内阳气,欺骗众鬼,但时效短暂;我二师弟听魅由古墓中获得了一本鬼术书,里头的化鬼术能让活人将阳气藏在膏肓之间,血液转黑,变成有意识的假死之人,足以欺骗鬼物、或者你这样的尸匠。」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不相信,事情太匪夷所思了!」
「不就是巧合吗?」不回眨眨眼,甩掉睫上残留的水珠。
季堂沉声,「你说说看,怎么个巧合。」
「喜神会前我就打听到,鬼山门的季堂是年轻赶尸匠中,最有实力夺魁的人,所以我偷偷跟踪,想找出你的弱点;没想到你居然也跑去找听魅,还折了两名尸鬼;听到你让随行师弟去找尸体,我立刻拜托庙里和尚演一出戏,成功到了你的身边。」
虽说是拜托,但根据猗傩派掌门师兄的个性,只有人家拜托他,哪有他拜托人家的份?他骗老和尚说季堂是江湖中有名的采花大盗,不仅采花,事後还会把人给杀了,平日则扮成赶尸匠来躲壁官府的追缉,身为捕快的不回,为了要人赃俱获,所以老和尚责无旁贷,必须帮这个忙。
「岛上你又怎么把我给制住的?我亲手给你换的衣服、梳的头发,怎么可能……」季堂说到这里,喉咙紧了一紧,盘诘的语调又低沉些许,「藏着让我动弹不得的药物?」
噗一声笑,不回说:「很简单啊,一照面时,听魅跟小师弟就认出我来了,配合演出了一场被我制服的戏;当你跟安国君苦战之时,听魅暗中丢给我一包鬼散,那东西能让你僵硬昏迷好几个时辰,等你醒来,我们已经跑远了。」
听到这里,季堂怒火中烧。
「……枉我……你居然如此对我……此刻你在我手里,我又该如何对付你?」
「别这样嘛,我虽然把你留在岛上,可还交代了你师弟去接人,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干脆一笑泯恩仇吧。」
说完,不回还真的给了个无辜又俏皮的笑容,好像一切真的可以就这么泯了算了。
季堂可没上当,他不是三岁小孩儿。
「你说的轻松,我却认为,千刀万剐都不足已泯灭我对你的恨意。」
季堂说的是真话,他对不回那思思念念的心情,就在今天看见面具後的那张脸时,冰消瓦解,虽然不清楚为什么猗傩派掌门长的跟不回一模一样,但他早就知道听魅跟猗傩派挂了勾,其中必定牵扯了什么他不知道的环结。
总而言之,他被设计了,他终于想通,始作俑者并非他早先以为的听魅,而是猗傩派掌门。
怨恨纷沓而来,但愈是愤怒,他的表面也就愈平静,他的确想着要将欺骗了他的人给千刀万剐,真的,他打算一刀一刀片去对方的肉,喂给山中的野兽,让血淹满一地,他还会拾起对方的骨头,一块块捣碎成灰,挥扬在山风里,千年万年都无法聚合。
从没有这么样的恨过一个人,因为……
因为……
今晚他蛰伏在猗傩派的山洞外,耐心、沉静,就算今晚等不到机会,但还有明晚、後晚,终有一天,他会遇到猗傩派掌门落单的时候,然後他会将对方解决得干干净净,同时也将心上的某一处,清理的彻彻底底。
因为……
或者上天是眷顾他的,他见到一个猗傩派的弟子出来,虽然戴着不同的面具,但是那身形及走路的姿势是猗傩派的掌门,不会错。
掌门不是独身而行,身後还跟着听魅那厉害的尸婢,但季堂也早有准备,他会让自己的负屈去应付含冤。
而现在,那人已经在自己怀里,一丝不挂,完全没反击的可能。
「想什么呢?」波俏的眼睛一瞥,嘴轻勾,含荡带笑问。
季堂突然间就口干舌燥了,冷硬的内心好像正在销溶,但他理智尚存,不允许自己失控;为了坚守这一点,一手反上,冷酷地掐住对方脖子。
「嘻皮笑脸,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