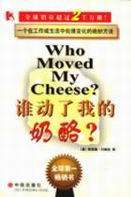行行好饶了我-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年前?!”她无法置信地杏目圆睁。“灯泡坏了十年你都没换?”
四海唇一撇,一副她大惊小怪的表情。
“所谓的‘客房’,不就是有人借住时睡觉的地方吗?既然进来就是要睡了,干么还开灯?反正是用不着的东西,何必浪费钱去换?”
想了三秒,她还真是无言以对,不过睡这种房间还不准开灯,她睡得着才有鬼!
“至少给我支手电筒总行吧?不然我半夜醒来想上厕所怎么办?”
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偷偷把手电筒开整夜吧!
四海没回答她,转身走进别间房,再出来时,手上多了一个铜制烛台,还有一根烧过的红蜡烛。
“手电简太耗电了,这是拜拜用的蜡烛,你就用这个吧。”
宝蓓从他手中接过烛台、蜡烛,和一个她以为早就绝迹的阿嬷级火柴盒,差不多觉得自己是跟古人借宿了。
“记得,省着点用,这一根是我半年份拜拜用的量,别给我用光了。”
“……噢。”
她看着不到十公分长的蜡烛,有些欲哭无泪。在这种房间点蜡烛不是更吓人吗?
不懂她思绪的四海自顾自地继续交代她:“还有,明天早上最迟七点我就会叫醒你,你最好在那之前想好去处,晚安。”
他说完便快步回自己房里,不给她求情的机会。不能说他无情,不这么做,明天一早八点钟,他雇用的钟点女佣一出现,装穷的事就露出马脚了。
“怎么这样……”
宝蓓噘起小嘴,这男人好像把她当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她有那么恐怖吗?
干咽了一口气,她先在门外点燃了蜡烛才进房。这么短一根,大概撑不到几小时就会烧光了吧?竟然还要她省着点用,根本就是不够用好不好,真不知道他是穷还是抠?
把烛台放在床边的五斗柜上,她立刻爬上床,一把抖开折好的棉被钻进去,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蜡烛烧完前入睡。
“咻——咻——”
说是这么说啦,不过当风吹过窗缝的凄厉声音不断出现,明灭不定的烛光又将房里的阴森气息加重十分;只要她一动,老旧木床就会发出“咿咿呀呀”的恐怖怪声,宝蓓越是叫自己别去在意,全身的听觉、视觉、嗅觉越是清晰敏锐,一点睡意也没有。
“吱。”
她竖直耳,那是什么声音?
“吱、吱。”
吓,那该不会是……
“吱、吱、吱……”
宝蓓立刻坐起,迅捷地取来烛台往周遭一照,一只又黑亮又肥大的老鼠,就在离她不到两公尺的地方,一副“你敢奈我何”的瞍样跟她大眼瞪小眼,完全没有钻回鼠洞的意思。
“砰!”
“啊——”
在身上的鸡皮疙瘩全站起来的同时,宝蓓下意识地把烛台往老鼠扔去,继而嗓门一拉,一声媲美世界第一女高音的尖叫响彻云霄,足够把刚进入梦乡的四海惊醒兼吓飞了三魂七魄,让他差点没从床上滚下来。
“怎么了、怎么了?!”
睡眼惺忪的四海一下床按亮灯,随手抓了门边的铝棍便往外冲。不会那么衰吧?真那么倒楣到家,才头一次带女孩子回家,就遇上了闯空门还想劫财劫色的贼吗?
“金宝蓓!”
他扭开门把直冲进门,已经准备好要硬着头皮“英雄救美”了,结果贼没见到,倒是瞧见窗帘烧起来了。
“不会吧?!”
他只愣了一秒,便立刻抓起宝蓓身上的棉被扑打窗帘上的火,好不容易才扑灭了火势。
“你干么放火烧我房子?!”
看着烧毁的窗帘和焦黑的棉被,屋里的火是灭了,但四海胸口的怒火可是正炽烈。
“有……有老鼠啦!”
她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还没消,一脸苍白地比手画脚告诉他。
“你不知道,你家养了一只好肥的老鼠,一直绕着我的床吱吱叫,我一吓就拿烛台丢它,结果它边叫边跑去撞墙,然后就不晓得钻到哪里去了。等我一回神,窗帘就着火了,我也不晓得会变成这样,好恐怖喔!”
瞧她快吓得魂不附体,不像是在编故事唬他,四海的怒气才渐渐平复。还以为她发起神经那么狠,自己的房子烧了,还恩将仇报,连他家也要拿来作陪呢!
“不过就是一只老鼠,你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他忍不住打了个呵欠。“没事了,那我回房睡喽。”
“不要丢下我一个!”宝蓓一把扯住他。“我不要睡这里,我要换房间。”
他皱了皱眉。“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其他房间都没放床,除非你想打地铺,不过那样子被老鼠咬的机会更大喔。”
她眼珠子一转,马上心生一计。“那我睡你房间,你的房里总有床可睡吧?就这么决定。”
“就这么决定?!”让她登堂入室还不够,竟然连他的房间都想霸占!“不行,我不习惯让陌生人睡我的床。”
她就知道他不会那么简单就答应,不过她也没那么容易放弃。
“难道你真忍心留我一个人在房里,被可能会再跑出来的老鼠吓得尖叫一整夜吗?”她捂着胸口,无限哀怨地浅叹一声。“唉,真的不行也是我的命,我的心脏一向不是很好,万一吓死了,就麻烦你好人做到底,帮我收尸了。”
喝,真的还假的?
四海头皮一阵麻。她要是真在他家出了事,有几个人相信他是做善事、收留陌生人借住?他肯定会上各大报的头版头条,更甭提如果真要他支付后续那些丧葬费用,那可是会让他有被“割皮削骨”之痛呢!
“我真是输给你了!”女人果然是祸水!“好啦,我跟你换房间就是,不用说些死不死的话吓人了。”
宝蓓忙不迭地摇头。“不是换房间,我们睡同一间,这样有人壮胆,我就不用再怕老鼠和鬼了。我们快走吧!”
她像逃难似的抓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飞快离开这间房,就怕慢一步又见到老鼠来“送行”。
“金宝蓓,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男的?”他终于憋不住问。
“有啊。”她边走边上下打量他。“你怎么看都像个男人呀!你这么问,难不成你是变性人?”
“我——”他气得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我百分百是个正常男人!我才怀疑你是不是女人哩?正常女人会硬赖着住进一个跟她不熟的男人家中,还主动拉着人家要同睡一间房吗?”
“不会。”她答得斩钉截铁。“不过你是好人,又不会把我怎样,没关系啦!”
怎么她的答案总教他有股很想去撞墙的冲动呢?他什么时候被归类为无害的好男人了?
“咦,你睡单人床啊?”
走进他亮着灯的房间里,映入宝蓓眼帘的是一间约莫有十五坪大的房间,里头却只摆了一整排的书柜、一张单人床、一张电脑桌、一个衣柜,再没其他东西,看起来空荡荡的。
“没错。”他甩开她的手,走到床沿一坐。“喏,就像你看到的这样,这么窄的床你真要跟我挤?那我们得抱着睡才不会摔下床喽。”
她走到床边左看、右看,不由得蹙起双眉。“嗯,真的耶。”
“是吧!”他故意说:“你长得又不像恐龙,我也不是柳下惠,如果抱在一起睡,十之八九会出事,你应该不想发生那种事吧?所以你睡这儿,我还是去睡客房比较好。”
对别的男人来说,这也许是飞来艳福,但四海自认无福消受。这女孩是熊是虎还不知道,他最好跟她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所以他话一说完立刻起身往外走,就怕继续跟她共处一室,早晚出事。
“等一下!”宝蓓又一把揪住他衣角,笑嘻嘻地说:“还有一个办法,我睡床、你打地铺,这样你就能保护我了。”
他额际浮现淡淡青筋。“嗳,你不觉得自己太得寸进尺了一点吗?我房间让你、床也让你了,还要我打地铺‘保护’你?你付多少钱请我呀?”
“钱?男生保护女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朋友之间谈钱太伤感情了,再说,是你家的老鼠吓到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跑来这间,你身为主人,保护我也是理所当然啊!不然我要是又被老鼠吓得心脏麻痹挂掉,你早上才发现也来不及了,所以——”
“够了。”四海双肩一垂,一副斗败公鸡的沮丧模样。“反正我说不过你,打地铺就打地铺,我去抱棉被过来就是了。也不晓得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
他边走边嘀嘀咕咕地回客房拿棉被。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明明车祸错不在他、她家也不是他放火烧的,可是只要她一摆出可怜兮兮的表情,他就是没办法狠下心撵人,真是伤脑筋!
明天,明天就算她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用,他一定要恢复“单身生活”!
清晨不过六点多,宝蓓就醒了。
她坐起身要下床,还好探下床的脚缩得快,差一点她就一脚踩扁四海那张俊脸。
蹑手蹑脚地按掉闹钟,她小心翼翼地蹲在四海身边,手捧着双腮,挂着甜甜笑意端详着那张孩子气的睡颜。
“早、安。”
她语气轻如柳絮,淡淡掠过他净白容颜,脸上尽是藏不住的羞涩笑意。
其实,这个男人还算不错呢!
虽然他又抠、又小气巴啦的,非但是开车撞她的凶手,还三番两次想丢下她落跑,而且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好像她身上有稀世病毒一样,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巴不得把她送上火箭射向外太空,今生都别再相见。
不过,他表现的是这样,做的却不是如此。表情凶、放话狠,骨子里却还是挺心软的一个人,咕咕哝哝得再不甘不愿,依旧是任她“予取予求”,明明就是个好人嘛!
再怎么说,他终究是没有肇事逃逸,住院时每天去看她、还替她付了所有医药费,昨天也是他死命拦着失去理智、一心想抢救财物的她,才没让她做出傻事;倚在他怀里大哭时,他轻拍着她哄慰的温暖感觉,也还留存在她心底。
再瞧他卷着棉被在地上呼呼大睡,一整晚君子得连她一根头发也没碰,这年头这么正派的男人真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
把他的优、缺点加加减减一番,宝蓓还是觉得他的优点多一些,而且他清秀斯文的长相又正好是她喜欢的型,如果他喜欢她、追求她,她可能真的会心动噢!
母亲生前老告诫她,看男人眼睛要睁大些,花书巧语、只想骗她上床的男人有多远踢多远;未婚又规矩的好男人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遇上了,一定要主动将人据为己有,免得迟一步就成了别人的。
难不成……这个钱四海是母亲显灵,硬牵来地面前给她“捡去配”的?
嗯,倘若她跟他真的凑成一对,那她不就能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白吃白住”?
呵,这样好像也不错耶……虽然现在想这个还太远了些,不过要是真能让她找到个又帅、又体贴的好老公,对她百般呵护,还供吃供住、解决她的困难,那她只要努力去赚弟弟的医药费,其他的民生问题都不用烦恼了,多好啊!
想了想,她轻手轻脚地离开卧房,先找着了厕所、借了他的漱口水一用、掬水冲洗了脸,然后便下楼找厨房,打算亲自做好早餐再叫醒他享用。
嘿、嘿,这么一来,搞不好他一时感动就答应收留她暂住,然后日子一久,真有机会让她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她边想边傻笑,经过客厅时,眼尾余光突然瞥见茶几上那本杂志的封面。嗯,她怎么觉得封面人物熟悉得很,越瞄越像是……
“钱四海?!”
她一个箭步冲上前拿起杂志看,那眉、那眼、那鼻、那唇,如果不是楼上那个三番两次在她面前哭穷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