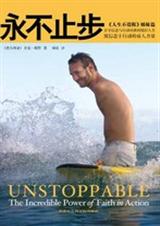岛1·柢步-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一语,只听见呼吸在抽痛里渐渐慢去,如同一条终于没有了动力的船。剩余的一切跟着消散,只留个完整的寂静无声。
整个夏天,总会在夜里因为腿疼而醒来。用手去抚摩,一块肌肉中了咒语般地僵硬。找不到施解的口诀,只能愣愣地注视着黑暗。似乎哪里积下更深的墨黑,哪里又削成薄薄一片。
盯得久了,恍惚以为自己从没有睁开过眼。睁眼的黑,闭眼的暗,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的还有,生成在身体某处的巨痛,和独自承受的静默,全都是同一种孤单。
孤单,孤单是。
孤单是一个人吃西瓜,一个人游泳,一个人的影子在地上比画出“SOS”。一个人唱歌或不唱歌,坐着发呆出神。
孤单是树上的雨滴掉在眼里,代替没有流完的泪。
孤单是电影院的冷气和自己,单人间的影碟机和自己,分手的别人和自己,拒绝的别人和自己。
孤单是买张50元的木头桌子,买把15元的木头椅子,想买床的时候不买了,因为不想再添置家具。
谁也没想过在这外头长久地过下去。
孤单是切西瓜,切得再难看也是自己一个人吃完的,丝毫不用有顾忌。
孤单是雨声,从天到地无处可躲,还有雷轰轰,还有闪电喀嚓,还有没人接的电话,没人知道你害怕得发抖。
孤单是咖啡色的皮肤,被晒疼干裂,而血液却因为逐渐凝固而变作纯白。
孤单是以为不难过其实没有,以为不疼痛其实没有,以为不会哭其实没有,以为能后悔其实不行。
孤单是三个半年里的四个夏天。说话也没人听,想听也没人说。只能自己对自己开口找话题:“怪声音”,然后又自己回答:“开着摇头电扇呢”。
孤单是晚上腿突然疼了,短短地清醒。
没有夏天,所有夏天,都在这里清醒。
传奇(1)
作者:落落一哪些是假的。
四季,雨雪。褶皱的海,正要开花。是麒麟还是饕餮,走过边界,变成倨傲凌乱的云。
不要提哪些是假的。发生在梦里的传奇,拼命罗列着美好和虚幻,以至连断句也毫无章法。只等白天醒来后,忘记了它们具体的涵义。如同分布在手掌里的纹路,零碎到找不到一条简洁的完整。所有吉普塞算命师都会对它们表示惋惜。
我知道哪些是假的。然后在白天想起会有些失笑。浪漫的图画式的幻想对于女生来说永远取之不尽,倘若王子的容貌还有千万种英俊的可能,那片永远盛开在虚无里的海,却总是一个样子。盛大的褶皱,袒露着它的排场,如同一朵花,边缘触摸到宇宙。
不知道目睹了什么,醒来后心里流过大段大段的字句。包括形容和陈述,甚至排比和问号,如同一个无知的灵魂找到了躯壳,要将前世最后的记忆统统留住,然后却还是指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只有凌乱的片段闪回在眼前。四季,衔接在一起。雨雪,天地纯白如往昔。海起了褶皱。因为风。麒麟或饕餮,究竟是麒麟还是饕餮,它们有什么关系。
直到醒来。天光暗白色,调和着昨夜的灰,爸爸和妈妈的呼吸声,从门缝里悄悄地隐入——拉弦般,一声轻,一声重,一声轻,接着停个空格,是爸爸揉了揉鼻子。
那些不是假的,我知道。翻个身,竹席的某块地方还未曾被体温占领,一片无力抵抗着的凉。楼梯上有脚步声。正往白天里踩去。
世界的一半在醒来后持续颓废的真实。自行车织过马路的空间,巴士气急败坏。圆珠笔用来书写发生于公元前的重大变革。卖水果的小贩拖住人说“那就卖给你,算我倒霉”。阳光照不进的死角里,有只母猫正在难产,她紧紧眯着眼,下身偶尔抽搐。
另一半却还有永世的传奇。我的梦里无需考辩真假。真和假都无法定义它。它们在画卷里繁衍,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墨点变作完整的故事。睡在河谷里的麒麟,或是性格暴躁的饕餮,踏下无声无息的松软脚印,鼻息里撞出动物的腥味。随后,车前子铺路,风信子出声,巨大的海,开出了纯蓝色花瓣。
那是我见过的最美最好的蓝。
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如此清晰地看见它。
二睁眼的时候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三日,早上七点。从梦境里爬出的身体,如同走出泳池,在一瞬感觉到史无前例的地心引力,身体沉重。
又是一个具体的梦。虽然每天都会发生。像是青春的症状表现。同样的还有莫名其妙的闲,无所事事的闷,以及精心雕琢的伤感。
小孩子,每天都要创造新的糖果,却不都是甜的。大部分是酸,是苦。像是要自讨苦吃。
得承认许多事都是自讨苦吃。敏感的年纪里留着大片空白,如果天天跑着,笑着,赞美万世万物,神经也会变成虚假的塑料质地。而它应该是纤细暖热的经脉,如同公交车网一般沟通起我们的所有感知。所以才会在那空余的时间里,变成忙于幻想和沉溺伤感的小人。
幻想出自己的传奇故事,而伤感日复一日地攻陷着没有守军的城池。
这些非常隐私的事没法子跟人聊,全都机密般地关在心底。乘着黑暗,它们反而更加蓬蓬勃勃。于是时光渐潮,靠南的墙上爬上了它们的青苔印。大片大片湿润的暗绿色,提醒着总有什么不可见阳光。不可去见阳光。
所以我从没跟朋友聊过这些东西。秘密一旦公开,就变成不偏不倚的笑话。身体里养着这么一个小怪物,出去见人,怕它的爪子伤了无辜群众。
平日里和朋友聊天,只谈偶像的新绯闻,只谈肯德基推出的早点粥,只谈去电影院的近路,只谈老师衣肩上的酱油渍,以为那是没有使用新碧浪的结果。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碧浪是否能洗走所有污渍,像广告里的那样。只是聊天而已,那些平常的话题,能随着发生环境如同变色龙般一次次更改它的模样。
传奇(2)
不断的绯闻,不断的新品,不断演出在明媚天日下的多视角故事,他身上的洗衣粉味,真实而温暖,浮动在可有可无的气息间。
很具象的年轻,投射在一点点造作和无数现实里。时间在上面悄然现形。我常常看见同一个角度下他的脸。眉、眼、鼻。后面的墙,白得粉质。于是人反而显得光洁,如同在一个平面里的像。在还没被冲印之前,所有颜色都在底片上颠倒。他的头发变成白色,眼睛流出白光,嘴唇灰绿,而世界漆黑一片。
我的神经就在这里缓慢而巨力地收紧了一下,从所有细微的枝末传向心脏。它像是被兜在茧里的蛾,突然获得了破壳的力量。
飞出去,衔起灭亡的火光。随后投进沉沉大海里,变成传奇的一部分。
粗糙的,柔软的,累计飞蛾们伤感的海。
三不知怎么我就是很容易想到海。当天走到尽头,地没入洪荒,还有一面海,变做世界的容器,盛下所有传奇。
世界的第三只眼睛,在宇宙里蔚蓝地闭合。
是因为在出生前,灵魂长时间浸泡在妈妈的海里的缘故么。那些留在大脑皮层里最后的一点隐约。眼下已经是如同幻想般含混而飘渺的画面。夜的天,昼的海,魂魄四下聚合,完成了最后的生命,浮现在羊水的大海里。如同酒窝。整个世界都在微笑。
妈妈的神话到此进入高潮,她扮演的女娲从水和泥里创造了一个心爱的小人。随后她就要褪掉所有神力,变成一个努力而平凡的女性,维护着所有大或小的生活意义。我在大的那一块里,或许是最大的那一块里。
晚上看见妈妈转身在厨房里洗碗,她一边说话一边往水里倒入洗洁精。泡沫、水流、利落的手指,窄小的水槽。
她早已不记得,在她古老的神话里,泡沫,水流,利落的手指,都在巨大的海洋里从容发生。那我就替她记着,夜夜看见它盛开如花,带着温柔的褶皱。
四所有的四季里,所有的雨雪,所有的海和惟一的花,不见了饕餮,不见了麒麟。
我们总以为自己年轻不可限量,拿“喜欢”做挡箭牌任意妄为。却不知道“青春”分明是个过去进时。
不断进行,不断过去。信誓旦旦的喜欢被轻松遗忘在脑后。青春所剩无己,谁乐意两手空空。
我们全都两手空空。
五传奇。
我是个在心里养着麒麟和饕餮,盛下满世界海水的人,以及两手空空。
这些都是真的。
飞鸟声(1)
作者:落落{※※在最后的夏天看见——有一千只鸟飞过头顶,翅膀交叠蔽日,光线暗淡风声呼啸,朝南的树冠被整个儿吹破,抵制显得徒劳。暴雨滂沱,漫山的红花溃烂在泥水,小路多处断开。}有根神经在脑袋的某个角落突然崩断,左眼一下刺痛无比。世界在这半边迅速模糊。另一边维持清晰。浅眠下意识揉眼睛,疼痛又突然没了影。手指落空,徒劳地绻着。
不止一次这样了,像是中了法术,细胞里埋着疼的种子,遇见水就会生出尖锐的刺芽,土地在血液里形成裂口,随后那棵花朵又去向无踪。浅眠没有见过那个巫婆,也不知道她究竟做了什么。她把这解释为太累。最近有好几次在电车上睡着坐过了站。
只有放学后的这一段时间,才像是被磨过边的,手感粗糙而安心。虽然最近眼睛莫名其妙地发疼,但大多数时候却也无碍。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回过头来看学校,那里就已经点起了为夜自修开的灯。学校一张黑脸,无数亮白的眼睛。
这个想法每次都得到反复提醒,并不是什么舒服的想象。以至于挤在车厢里,反而会让人不禁舒了口气。车厢里有许多味儿,更因为是冬天全被堵在窗户里出不去,便在人的身体内外循环——挎包的牛皮味、围巾的毛味、还有塑料袋里的水产腥味全都融汇掺杂,最后就化学反应出了整个傍晚的味道:倦怠和疲惫,织上迅速褪去的暮色,拥挤的空隙里没有意外和突然。
时间是能在味道里停止的。偶尔有这样的错觉。
尤其是当电车进入隧道,江底的潮湿粘合地搅拌空气,光线在头顶平行消失,视界里迎来变成暗红色的国度。不是血块的暗,也不是嘴唇的红。每个人的脸都像被镀上面具。厚厚一层,涂着勉强的形容词。那些面容突然显出前所未有的忧伤,在温柔的暗地里缓慢变化。像是假的。又或是最真。
浅眠在这时看见了转向自己的一张脸。额头、发线、眉梢边的句点;没有表情的忧伤,在视线里绕成矛盾的盘结。
他的眼睛落在上面。半浮半沉。
浅眠微微张了张嘴,整个心里无声无息。
{※※月亮红色,瞳孔紫色,潮水盖住脚面灰色,指关节绿色,向日葵园黑色,向日葵们统统黑色——在最后的夏天看见,一千只鸟飞过的地方,死去的森林复活,一片银白色。}冬天的所有都遍地银白。掉下一根头发也会留出纤毫的轨迹。人在上面快乐地奔跑,脚印歪曲指向钟楼。抬眼看的时候,时针分针并合,宇宙在上面保持完整,所有星星宛如尘埃。须臾拼接永恒的长度。
眼睛又刺痛了起来。
等到放下手,车已经开上地面。像谢幕后的演员,满车的人都回复了之前的样子。妇女的笑容尖利,睡在座位上的人有着死去般的安详,小孩子的嘴角保持着天然的残忍,高亢地喊着话。浅眠慢慢转动视线,寻找之前的那个男生。
额头,谁的额头;发线,谁的发线;眉梢不完结,表情复制成多份。浅眠找来找去见不着,想要换个位置又被堵得严严实实。突然冒出的焦急在两头扯着心脏,手腕上的脉搏留下密码,却无法解读。
直到他再次扭头看向这里。
清晰的额头和黑发,眉毛以及眼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