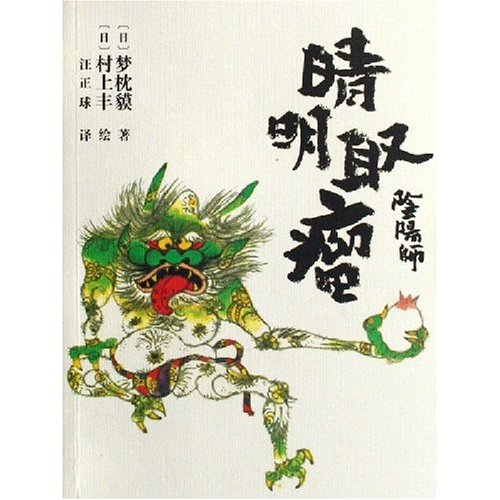阴阳脸-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画虎雕龙染翰,高山流水弹琴”的自矜,以及《戏咏不倒翁》中间两联“何妨失足贪游戏,不耐安眠欠老成。尽受推排偏倔强,敢烦扶策自支撑”的借题发挥,这些作品中的牢骚与自重身份应该不难看出,而写作它们的人却自称是一位“绝意仕进”“藏名变迹”的高士,这一点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复社大会
虎丘位于苏州西南近郊,远古时期这里曾是惊涛拍击中的一座小岛。两千五百年前一位悲剧人物伍子胥在山下的王宫内指使刺客专诸暗杀了吴王僚,同样的传奇故事也许还要加上继位者阖闾死时作为殉葬品埋于地底的那三千柄锋利的宝剑,这使它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一层与周围的温山软水极不相谐的悲壮色彩。明末的著名党社复社选择这里开始它最初的政治历程,想必不会出于偶然。尽管崇祯十四年领袖张溥的逝世以及稍后明室覆亡,异族入主等变局,令它的影响一度降至冰点。但经过顺治七年有吴梅村、徐乾学等在嘉兴参与发起的十郡大社,鸳湖会盟,一时间又隐隐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一次不合时宜、突如其来的高潮出现在三年后的一六五三年。在这一年的上已春日,数千名复社党徒借踏青为名突然在虎丘聚集,召开该党历史上规模最盛的全体党员大会。“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在满清政府已对民间结社集会关注,并加以密切防备的局势下,任何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到这样授人于柄的招摇无论时间上和组织上都很不策略。这一点也曾令后来不少研究者深感困惑和不解。但如果我们试着将整个事件视
作一个谜面,而谜底是数月后吴梅村的入仕新朝,相信一切疑问都会变得迎刃而解。
事情看来也真是这样:复社在虎丘炫耀势力之日,正是吴梅村决定出山之时。云岩塔下的千人石尽管只是印证佛家无边法力的一个原始场所,但在现实中却被精心设置为通往权力巅峰的重要台阶。尤其是大会上如愿以偿选出了“奉吴梅村太史为宗主”的新的领导班子,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原先计划中的意图与效果。从现在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吴终于打算与新政府合作的决定甚至早在此前一年就已经作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与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官擢内阁大学士,正式进入了朝廷的决策核心有关。当时隐居河南、曾与他相约有“决不仕清”之盟的好友候方域闻讯后曾立即来信力阻,一位尊敬的长者——吴中高僧愿云大师在和他《西田赏菊》一诗中也有意以“独擅秋容晚节全”七字作结,含相劝之意于言外。但为等待这个时机已准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的吴丝毫不为所动。相反,他不仅借寓嘉兴万寿寺写作《绥寇纪略》一书作为进身之阶,还指定他的弟子王淑士、周子淑担任联络招集工作,亲自策划并主持了此次大会,其真正目的显然想以文坛盟主与在野党领袖的双重身份作为筹码,向他未来新的政治主人索取更大的回报或赏赐。相比于与他一同名列清初文坛江左三大家的另外两位钱与龚的立即效忠新朝,吴忸怩作态的十年退隐说穿了不
过胃口更大——一种欲擒故纵式的待价而沽——犹如宋诗“永巷深日闭娉娉,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里描述的那种曲折艰深的意境。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卖与不卖,而是怎样尽可能卖出个好价钱。也许,以一代诗史、前朝显宦、二十余岁时就已开始名扬天下的吴一贯的矜持与自负,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有苦衷。
在苏州虎丘的热闹场面一个月后又出现在嘉兴,同样的轰动,同样的慷慨激昂和诗酒风流。在后来读者的想象中,这些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人,通常被描绘为面容朴素,精神高远,犹如金庸笔下的天地会会众或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革命志士,这显然应该是个很大的误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过是些标榜声气、寻事滋非的家伙,“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事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朱一是《可为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读书应试大多名落孙山,崇尚政治除了狭隘的党争之外也没有更深层次上的理解。尤为让人难堪的是他们对权欲与女人始终怀有的空前高涨的热情。干革命时“中列倡优,明烛若繁星”那还是小事,一度甚至还有反清复明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秦淮某著名花魁妓楼内的浪漫传闻。说到他们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那也基本上和他们的领袖吴梅村一样,在野则逆,在朝则顺,所谓民族、节气这样的大事仅以一已私利胡乱论定。因此,在几年后清廷兴起的“通海案”“奏销案”中,该社的政治基础迅速瓦解,消声匿迹,这一点应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当时的大众舆论对这些家伙也不看好,以至在一则记载中——作者于复社集会之日正好路过虎丘——曾出现了如下辛辣无情的调侃与讥刺:“太仓
吴梅村祭酒伟业以明臣降本朝,当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第三章
吴梅村事略(5)
贰臣
封侯拜相这一生平宏愿在异族统治下的新政府内即将成为现实,我们已经知道其间花费了吴梅村将近十年时间。这只前述箱体运行的股票在看准时机并有实力庄家——朝中重臣陈之遴——承诺托盘后,现在终于在万众瞩目中突破长期盘整的平台放量拉升。但紧接着发生的一切不仅大大出人意料,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显得相当滑稽可笑。就象一个满心打算坐飞机头等舱的乘客,最终到手的却是一张长途大巴的普通车票。在北京,吴以不惜牺牲士望与清舆的代价换来的报酬,竟然只是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从四品的秘书院侍讲一职,这个职位甚至比他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小了半级。而且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也“仅委以编书,所谓‘虚相位以待者’竟无其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多年的惨淡经营一朝顿成泡影,顾盼自雄的商鼎周彝只卖了瓦釜的贱价,这对一向善于以谨小慎微的表象掩饰其老谋深算,不轻易出手的吴来说,该是如何残酷和毁灭性的打击。“误尽平生是一官”!“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吾病难将医药治……竟一钱不值成何说!”这以后这样一种自怨自艾的情绪一直纠缠在吴的内心,尽管这对他后来诗文的成就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几乎与十七年前错判局势的那番引人注目的表演如出一辙,在“朝廷屡召”“两亲流涕辨严”这样的借口下面,顺治十年吴的所谓扶病出山说起来同样也是政治斗争的附带产品。在当时仕清的汉族权臣中,陈名夏、陈之遴的南方集团与冯铨、刘正宗的北方集团为向朝廷争宠一直斗得不可开交。趁此机会推出名满天下,且久有跃跃欲试之心的吴扩充自身势力表面上采取“江南总督马国柱具疏举荐”这样的形式就计划本身来看,不失为他女儿的公公——朝中权臣陈之遴颇为自得的一着妙算。但吴的不幸未被重用不仅令当事诸公始料未及,在后来研究者的眼里也几乎成了一桩悬念多多的疑案。在找不到其它对他明显不利迹象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吴临行前在虎丘的一番招摇客观上很有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年后局势再度急转而下,由于他的两位官场靠山被人以谋逆罪名告发,分别以被绞与戍边的下场匆匆结束其政治生涯,吴在京师的处境于是显得更为岌岌可危。
谈迁的《北游录》是记叙吴在京生活最详最确的文本。此人比吴晚几个月,于公元一六五四年正月以高级幕僚身份跟随弘文院编修朱之锡到京任职,并因写作煌煌历史著作《国榷》,经著名藏书家曹溶介绍与吴相识。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两人之间因学术交流有上百次的来往记录,包括采访、研讨、闲谈与聚饮,地点大都在吴北京的寓所之内。通过对他的这部日记体作品的仔细析读,一个消极失落、郁郁寡欢、整天靠读书与应酬打发日子的吴的形象几乎呼之欲出。其间甚至还生过一场大病。据周黎庵先生《清诗的春夏》一书披露,此病的来由竟然是因为爱妾为某满族王亲公然恣横、劫夺强占。“吴伟业自为不堪,然又不敢抗争声张,忍声吞气,不免抑郁成疾”。如果此说可信,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已到了如何可怜的程度。两年后养母汤太淑人病重垂危,吴已多次请求的辞职一事这才终蒙恩准。四年的贰臣生涯犹如南柯一梦,帝王的戏弄、权戚的强侮、清舆的耻笑、青史上的污点,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错判形势、轻举妄动的憎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足以令一颗自己感觉良好的头脑从此循规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份之想。
奏销案
根据孟心史在《明清史论著集刊》里的综合研究,顺治十七年末祸起无端的江南奏销案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国家税务部门行使其司法职权——追缴江南各省民间历年所欠之税粮,其真实用意却显然与政治有关,显示其时政局已得到初步巩固的满清政府终于打算腾出手来,整肃登基以来思想领域的混乱状态,拿其中某些不大肯听话的汉族知识分子开刀。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一书也认为,此事系“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这与此前发生的“科场案”“禁止结社”“哭庙案”和稍后“庄氏史案”等遥相呼应,丝丝入扣,无论从手法与时间的安排上都不妨视作一个精心策划的整体。以局外人的观点来看,统治者在政局稳定后固然无需再笼络人心,但当时蔚然成风的缙绅世族横行乡里,目无官府,以及如前述复社大会那样的招摇,可能也是其中的部分诱因。
也许我已将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刚心灰意懒回到贲园不久的吴梅村在事件中的不幸遭遇吧!当时他和当地几乎所有乡绅士民一样,既长期拖欠税款不纳,同时对此事后果的严重性也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事先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北京政府突然颁布法令严饬各地官员克日收缴、违期法办。根据现存部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吴所在太仓州的查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其时全州“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抚臣欲发兵擒缉,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锒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黄庭表……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这个过程反映在吴后来自己的遗嘱里,也就是“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素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那一段怨恚之言。尽管身陷囹圄的吴最终经人营救,设法主动补齐欠款而未加任何处置,但其间的羞辱与狼狈一如几年前的那次自为得计的东山再起,相信令他的精神与肉体都被迫承受了终生难以修复的沉重打击。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