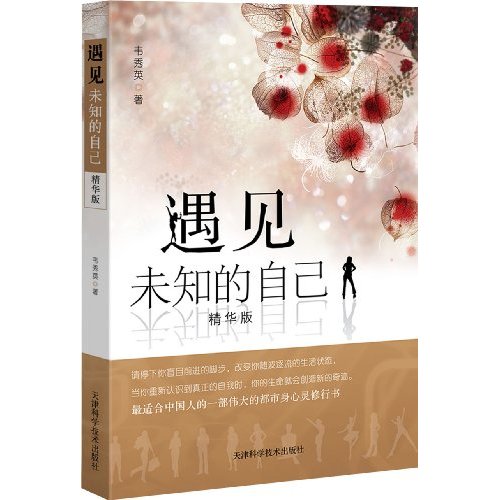�����Լ�-��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ҵĶ����������ص绰Ҳ�������ˣ������ѡ�ͬ�»����Է����š����ʼ�������������ʹ����Dz����ٸ������绰�ˣ�����������绰��˵���Ƕ��DZ�ϲ�����ǵĻ������Һ���û�еڶ����������Խ����ˡ�������ʼ����ʱ���һ����̲�סҪ��ͨ����ĵ绰����֪�������ȽŲ��ã�Ų���绰��ǰʱ��Ƚϳ��������Ҷ�ϰ���õ绰�����һ�ᣬ��������Ϊ���Žӵ绰�����ΰ������绰�����ŵ�ʱ���Ҽ�ϣ����������������������������ʱ��绰���˺þ�û�˽��ҷ����᳤����һ������ĬȻ������÷�ʪ����Ͳ�����绰�����ʽ�Ѿ��㹻�ˡ�����ڵ绰������ʵֻ������������������Ҳ����������˵�Ҷ��ã�������æ������Ҳ�á���������˶���Ҳ�е㱳��������ǿ���ˣ������������������ҵ����������壬�������dz���ɤ����˵����˵������Ȼ��������������˵��ʲô��������������߶߶������Ҳ���˰ɡ�
�ҵ�����Խ��Խ�����ˣ��һؼ�Ψһ�������ܵĺ����ļҳ�Ҳ�����ˣ����������Ա߿�����˵�������Ҳ�ܹ���˵��ʲô�������н�����Ա߰���˵�Ļ�д��ֽ�ϡ����������������ߣ���������ֲڵĴ���������ǰ���������������ţ�˵���������滺Ѫ�����Dz��ǻ�Զ����Щ��˵ʵ���ҴӲ��ǵ����豧���ң���ô���˺����һ�κ������������ܽӴ��������е㲻ϰ�ߡ����������˵ʲô�����������ܼ��ˣ�Ҳ�ܷ����Լ�Ϊʲô���������أ���ֻ��Ӳ����˵���裬�Ͻ�˯���ɣ��л�����������˵����������������������۾�����ô��������ġ��Ұ������ñ��ӣ�ת��װ˯����֪����һ��Ҳû˯�⣬�����������ң�����û�а취������ԡ�
�����䲻ʶ�֣����������״������������˼��ų�һ��ʮ��Ҫ���㣬����������ȫ��ÿ���˵��������գ�����үү���Ұ֡�����ÿһ�����ӣ�������һ���ĺ��ӣ�����������������˺��ӣ������µ�����һ��Ҳ����©���ҵ�һ����鳤��20���꣬������ȥ����ŷ��־�Ȼ��֪���Լ������յ�����ʲôʱ�����������Dz��Ǽǵá�ÿ���������Ҫ�������ˣ���������Ϳ�ʼ��߶��������ûʲô�Եģ���Ҳ����ٱ����óԵĹ��������գ��������������Լ������ա�������ô�ຢ�Ӿ�Ȼһֱ��û��֪���������������һ�죬ֱ�����������Dz�����ҲӦ�ø��������հ���żȻ˭��������������һ�������ܸ��ˣ���������������鷳������ʵ������ϲ�����ֵġ��ҷdz������������Ҽ��Ժܺã����źܶ����ѵ����գ�����һֱû��ס��������յ��������죬ֱ������80���ٲ����ڼ�ס���������ա���1929����³��š�
����˵��������������Ӳ����������һ�����ۿ�û���ˣ�����ү�Ѿ������ӵ����ϵ�һ�Ѹɲ��ϣ�ֻ�������˾;���ȥ���ˣ�û�뵽�������ŵĿ���������Ȼ�ֻ�����ˡ��Ұֻ���ʱ��������˵������һ�仰����Ϊû�Ļ����Ұ֡��ڽŵ�������һ���ӡ����Ұ�ȥ���������ٲ����ˡ���Ȼ�Һ��Ұֵĸ���������������Լ�Ϊ����Ϊ��ĸ֮��ÿÿ������������������̲�ס�������������ͼ���ʵ�ͽ���ũ��������һ�����߲��������꺮��ů�������˰����ֵ�������������Dz��ǻ��̤ʵ�أ��������Ҵ���ӵ�Ȱ�棬����������ĸ����������ߣ���������ʱ�˲赹ˮ�ź���ӣ����Ͳ������������˰ɣ�
����һһ�����¶�ʮһ������ʮ����
���ҵ�һ����ү
�ҵ�һ����ү
�����ϼҰѰְֵĹùýйã��ޣ��ţ��ѰְֵĹø��й�ү��ү������������ү�����Ƕ�Ů���ijƺ����������������
��ҹ�ү��ʵ���Ұְֵı��ø�������������¸����أ���Ϊ��ǫ�ͣ���Ϊͬ�ö����Ե�ʣ������ҰְֱȽ����������Ǽҵij��͡�Сʱ���Ҳ�֪�������Ҽҵ�ԨԴ��������һЩԵ�ʡ�
���������������һ����������ǻ������������Щ��ϧ���Ҳ�̫����Ϊʲô�������������ͱ�����ݲ�̫һ��������������ЩСë��ʱ������������������һ��Ƚϳ�Ȼ�ĸо���
�����Ǵ��ŷ��Ļ�ɫ��ɽװ��һ����������ɫ������������������εøɸɾ��������˱�ֱ����ÿ�����������ĵ�����������ճ���ô������С���Ӷ���ô������������˵�����Ļ����Ե���ô˹�ġ�
�������Dz���ʮ����·�ӳ������Ҽң��Ӳ�����������һ�����˼ҽŲ������������ֽ�������߽�Ժ������æ��������������û�а����Ͻ���������������Ҹ��õ�ı�������һ���Ұֵ��²衣
�����ҼҶ���DZ�����ֻ����Ժ���ﵽ��תת���������������еظ���˵�ҳ���̣���ֻ��רע���ţ���Ŷ���ޡ�Ӧ�ţ�ƵƵ��ף��������ԡ������Ұ־�����һ�ᣬ�ȵ�裬����˵˵�������ʲô�飬żȻ��̾һ�����¾����ˣ�Ҳ�������������Ҽҵ��������ܻ���ȥ��Զ�ĵط�������Ұ��һ�㡣
�������ù�ү���Ұ����ȣ�������үǰ���ߣ������žͿ�ʼ�����Ұ֣����㿴�㻹����ø�������ô�ϵ��˻������ߣ��������˳�ȥתת�������Ե�������Ҳ��ȥ�����絽����һ���������ڿ��ϣ����˳Է����߲������ǿ��飬�۾������ˣ���Ҳ�ɵ�ɢ���ˡ��������������߶���Ұ��Ѿ�����ʮ��ĵֿ����������������������һ�£�����˸���Ӭ�Ƶģ�̧ͷ������һ�ۣ�������ת���泯ǽ���ţ����ű������ڱεĴ������ǵ�����������������ġ����顱�ˡ�żȻ���˵�ʱ���������������ϵ�ľ������飬������ȥ���Σ���˵���ĸ߶Ƚ����۲���ʹ���ù���ʪ�Թؽ����Ƚ�Ҳ�����㡣
�Һ�����������ȥ����ү�ң�������ˮ���������������ڽз��������Աߵ�һ�������Ĵ�Ժ�ӡ�����˵�����ҳ�����û�¶�������������ǽ�Ϸ���Ƭ�IJ��������ᄍȻ�к�Щ�dz�ģ������Ƭ��������̼�ػ�����Щ�˶���Ϸ̨�ϵ���һ�����ų��������Ź�ñ���Ҿ�����Щ��֡��ҺͰְ�˵���ҿ�������Ƭ���Ұֲ�˵����������峯�������٣���ү���ǰ��������ˮ�����IJ��ӡ��鷨�ң�����Ϊ������ͼ��������ź���˺ܶ��ͷ��������˳������ϧ��һ���Ż������ְ�˵�������һ����̾��
˵����ү����˵����үү����үү�����Ϊ�Һ��ŵ�Ե�ʺ��Ұ��и��ң���һ���������Ұֵ��Ų�����һ�����߶�����������С�����ܵ���Ԫ�⣨��Щ��Ԫ��֪��һֱ���ڼ���ʲô�ط���үү�ߺ���꣬�Ұ־����Լ�Ҳ���˾�ƽ�ָ������߸��ֵ����һ��ʮ�����Ұ�˵����үү����Ѫ��ϣ�����������������룬ʲôʱ��Ҳ��Ҫ����Ǯ���ˣ�������һ�仰����һ���Ӷ�Կ�������ʱ����ߵÿ�һ�㣬�ܵ�����һ�㡣����үүһ���Ӷ��ڼ�����仰��������ʱɨ������Ժ�ӣ����ں�ǽ��ɹ̫����������ר�Ÿ�������һС����ȥ���Է�������������ǽ���Ѿ��е�Ӳ�ˡ������Ϊ��үү�Ƚ����壬��������Ҳ����ȥ�������Ұ��趼��һ���ŵ��ȳ������ҹ�ү�����ĸ����š�������Ļ������Ⱥ�ʱ����Ͷ��·�������Ҽ����᷿�����һ�����£��ܹ����ҡ�
�Ұ�������үү���Դ����̣����˵�һ������������������Լ��Ա��˵ĺ�ȴ����٣����ڹ�ү���Ҽ����ѵ�����ֻ��˵��һ���Σ����轲�������Ե�ʱ������������£�Ҳ��ϧ��ү����Ϊ�˲��ô�����֪������ү��������һ�����ţ����������ͳ��ͺȡ����������ү�ʵ��j�̵����Ӻ��������Ҽұ������µĸж����Ͼ����Ǹ�Ǭ���ߵ���������Σ���������˷�Ŀ��ʱ���ҼҶ��������Ԯ�֣���������ȫ�ıӻ����ȷ糱����ƽϢ���������ӹ�ү�ؼ�ʱ���ڵ��ϸ���үү���صؿ���ͷ�����������������ҼDz�����ǰ������̫��ϸ���ˣ���������������˵��Щ�£��´λؼ��Ҵ���������˵˵�����ҽ����ұ�¼������
��ү���Ǵ��˼ң����и����ü���������������ģ���˵�����������Ϲ�ʮ���и�С¥���Ұ���������ѧʱ����ȥ�Է����Ұ�ʱ��˵���������Ĺùø�������һ��ë���·���Ҫ֪���ڽ��ǰһ��ë���·����Ұֵ���ͬѧ���ж����ۡ���������Ƭ����Ϊ֤�����½Ǵ��ű�ͦ��ë���·�������Բ���۾����Ұְ���ͬѧ���Dz��DZȽ������ʵģ��Ұ��Ǹ������ˣ�������ʱ��ͬѧ������˵����Ƭ��û����ͷ�У��Ұַ��ĸ�����ÿ��һ�ţ������Ŵ���Ǹ�ӡ�ģ���̫�����������趼ʱ�����䡰��һ��ë�����ѡ�����ү����һ�����ü��������Ұ�76�����Ҹ��ڱ����β�ʱ���������ùã�˵��Ϊ�˸��Ҹ���ҩ�����ǰ��������ùõ�һ��Ů���������������г��������ܣ����Ѹ�����ι�̵Ķ����ˣ��Ұ�һֱ�����Ǽ���������飬ʵ����Ǹ�����ֲ����ҹ�ү����һ�����ý��û����ɷ����ˣ��ص��������ϣ����ܵõ������ϧ����û����������С��ɩ�Ӱ��ۡ�
����˵���ү�ң���������һ�����������Һ͵ܵ�ȥ�����ݵ��龰�������ү���Ǹ����ˣ�����������ѽ������������˵��������ů������ĺ����ƺ���û��ɢ�������ݼ��ܵ��ķƱ������̹����ġ������ۿ��˼Ұڷ����ˣ��������Ů���˲�û�����͵���˼����үȴ�ܸ��˵�Ҫ�����dzԷ������������������һ�ۣ�������ʹ�˸���ɫ������һ���dz�֪Ȥ��ǿЦ�ŸϽ�������ץ���Һ͵ܵܵ���˵�����ˣ�����˳ˮ���ۣ�Ц��˵�ǾͲ������ˣ��´������ɡ�ľګ�Ĺ�үû�з���Ů������Ƥ���µİ���ӿ������ִ��Ȱ���趼���Է�ʱ���ˣ���ô���������ߣ�����ֻ��������˵��Ҫȥ�������̼ҳԷ�����ү����˵��Ȼ���²��Է����Ǵ����ĸϽ��������Ҹ�ƻ�����ϣ�����Ů���ٳ�û����ֱ�������߳�Ժ�ӣ��ߵ��������ͷֻ������ү���ͳ��������и�ƻ����Ӱ�Ӱ������赹û̫�����Ǹ�ƻ����ֻ��˵���㲻֪�����ү�ж�Ϊ�ѣ�����ɶ���ˡ���
�Ժ�����ѧ�ڼ�ʱ�䲻�࣬���������ү���¶�����������˵��
������ϵ���ͺ���Ա�����ݿ����ؼ������ˡ���ү�Ѿ�����ѧ�����ˣ���Ƹȥ��ʷ������ˮ�ط�־���Ƕ�ʱ������æµ��������������ζ�ؽ���Ұ��ղص�һ�����а��ɹ�������ñ��ȥ��֤����������˵��ү����ѡ������Э�������ȡ�
��ү���Ҽ�д��һ�����á��������IJݣ��˼������硱����Ӧ�Ұ�Ҫ��д����鹡�ͨ�µڡ������ֿ�������Щζ���������ºܸߵ�ʱ�����д��һ����������н�����������ǿ��Ϣ�������������ҵ����������Ϲ������鷨�������㲻��̫�ã���֪�������Ĺ�����Щ��ķ�̫������ϵ�Ե�ʡ������֮��۾�����Ҳ�֪�����Ĵ�������۾��ʵ���������鷿��һ���ªƽ����������ô�����ŵ����֡��Ҳ����ֵ��֪����۾����QU���ǡ��Ϳࡢ���͡���������˼����ү��һ������Ĺ������Ϳ࣬ȴ���Ͷ�����
�����һ�μ������벻������һ���ˣ������Ǹ����ģ��һؼ�̽��ү���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