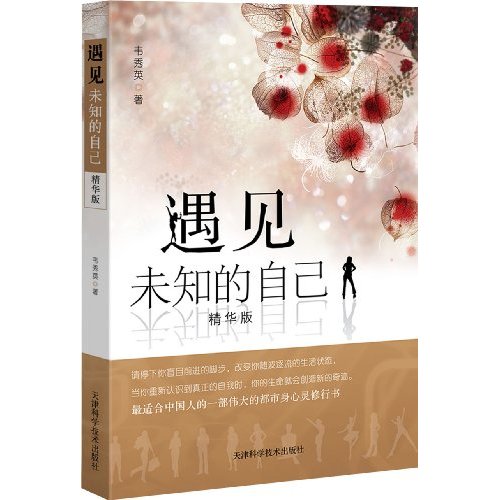倾听自己-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
⌒ ∨
(﹏)。。 (﹏)
╰╯
妈妈和老院
寂静之声(处女作)
2011年5月8日,82岁的妈妈终于如愿回到乡下的老院子去住了,她不知道这天是西方的母亲节,只是碰巧姐姐们有空送她回去,帮她洒扫庭除,把她一个人安顿下来。
爸爸在6年前的4月去世,之前他总是喃喃自语“人老了,就像树叶一样,要落了”。看着父母日渐衰老的身影,我却总愿意相信他们会一直好好活着,活在老院里,时刻等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推开院门,我怎么也想不到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向硬朗的爸爸因为脑梗猝然倒下。我赶去奔丧的夜里,还没进门就听见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嚎,看着满院临时高高栓起的亮晃晃的灯,纷乱的人影,树下摆满的桌椅,我不得不相信对于我和妈妈而言,天塌下来一样的事实。尽管爸妈几十年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但大家都担心妈妈捱不过来,所以我跌跌撞撞进门,是先奔去妈妈面前,和围在她身边亲邻一起劝她“千万要好好的啊”,然后才去看爸爸,给爸爸守灵的。爸爸的脸上已经盖上了黄纸,双脚已经直直地被用红绳绑在一起,虽然他的手还温热,但天人相隔,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世界也从此残缺了。我至今忘不了妈妈的泪眼,她总是捶胸哭喊“你为什么走在我前面了?老天为什么不长眼睛,把那么好的一个人带走了,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可可怜怜地活着,让我以后可怎么办呀”,别人劝她“你们在时还不是老吵嚷,再别想他了吧,以后孩子们还要靠你呀”,妈妈一点不理会地说“我们吵是吵,心事和的,我现在和谁去吵呀?我端起饭碗就想着他劝我吃饭呀”。那段日子,她执意要一个人守在老院子,直到过了爸爸的百天忌日,才硬被弟弟接到城里。但以后每逢爸爸周年忌日、冥诞、春节,她都要回去住,虽然她腿脚不好,懊悔不能亲自去半山的坟上看看,但起码她要等着儿女从坟园回来,告诉她坟上的柏树栽活了、长起来了。
妈妈在弟弟家其实像个辛苦的保姆,她天不亮就起床烧水、煮牛奶、蒸鸡蛋,等着弟弟的孩子起来,然后扫地、擦桌子,忙乎一天的三餐。弟弟是妈从小惯大的,所以即使已经年近四十还是四手不抬,等着妈妈端吃端喝。有一次妈妈说她数落弟弟的孩子贪玩不好好学习,刚入小学的孩子竟然顶嘴“你吃的我家的,住的我家的,咋还骂人呢?”妈妈笑着嗔怨“这没良心的小贼,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他,谁想他说这样的话”,弟弟弟媳一再解释他们没有这么教,我不知道妈妈强撑的笑容下隐藏了怎样的心凉。
姐姐说,听说我“五一”假期要回来,妈妈十多天前就让把她从弟弟家接过来,想着我回来住方便点。弟媳妇和姐姐们关系不睦,每次周末、过节团聚在弟弟家,大家多有不便,连姐姐买的菜弟媳也不吃,很让妈妈为难。不过我回去也就匆忙两天,只要妈妈在哪我就陪她在哪,住哪都一样的。我担心妈妈离开弟弟家,他们孩子放学怎么办,弟弟会不会不悦,觉得这是因我而起呢?姐姐说“弟弟家的事也帮不到哪去,妈到我家来我帮她洗澡也方便点。”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妈妈不会又不想在弟弟家住,想着要回去吧?
我乘坐一大早的班车回家,中午12点时我发短信告诉姐姐已经到了郊县,应该再过一小时到达,姐姐说妈妈已经做好饭等我回来一起吃。我想她肯定又是大清早起来,做完早饭不停歇地忙中饭的吧,可是我什么点到还没准呢,我让他们先吃,我回来再吃。班车出了高速堵在还没修浚的路口,进的车、出的车困成一团,挤在窄乱的村路上,我只好眼巴巴等着,看着赶路的摩托车在一动不动的车流缝隙里艰难穿行,恨不能下车自己步行了。我告诉他们堵车了,什么时候到不一定,让他们别等我吃饭了。我到时已经2点半了,姐姐在车站接我回家,一进门妈妈迎上来,看着她还算精神的样子,我路途的疲劳也基本消失了。妈妈探询地问我“你的耳朵咋样了啊?”虽然我的听力因为听神经瘤每况愈下,但我搪塞她“嗯,还好着呢,就那样,你不要担心了”,我可不想再吃她到处求神问药找来的偏方了,比起她的迷信,我宁愿相信“科学”,尽管科学也治不好我的病。
姐姐端出第一碗饭到我面前,是乌龙头(老家的一种野菜芽,状似毛笔头,味道略清苦)打卤面,多么熟悉的饭食啊。面条自然是妈妈手擀的,虽然她已经佝偻着背,手指也变形了,眼睛也花了,但还是能凭感觉切出挂面一样细、一样匀的面条。我们总劝她再不要手擀面了,买面条又便宜又省事,她总说“只要还有一口气能干动,我还愿意干活呢”。等我理所当然地大口吃着,才发现妈妈、姐姐才端上饭碗,我想发火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先吃,非要饿着等我到这会,但看着他们自然的表情洋溢着欢聚的喜悦,我就着面条,咽下了我的怨言。
放下饭碗,妈妈坐到我跟前,费力把椅子挪近些,她怕我听不清,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要回去哩,回乡里去”,有点讨好的样子,像个孩子在央求我的同意。妈妈老了,凡事自己做不了主,有想法还要说服儿女们大家同意,尽管有时孩子也是为了她好而劝阻,光说要回乡下去住已经说起好多次了。我说“你现在年龄这么大了,腿脚不好走路都摇摇晃晃,老院子的台阶你上去都费事,自来水也不方便,那么大院子你一个人住多害怕啊”,妈妈露出很坚强的神情说“咦,我一个老太婆怕啥呢,我不害怕!”听着她轻描淡写的话,我心里却像堵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却让一个老人独居不是个办法呀。我小心问妈妈“那再不去弟弟家了吗?”她顿了半天,叹了口气,“我再不去看那眼色了,我这么老的人看眼色干啥呢。我做的饭人家不吃,你弟媳老在外面买着吃,你弟弟对我说话口气也不好,媳妇能好吗”,说完这话,眼泪从她虽然苍老却依然明澈的眼里渗出来,我伸出手,默默擦去她脸上褶皱里的泪水。看来这次她是真的伤心了,那弟弟家不去了,就在姐姐家好好住着,等天气好了再说吧,今年天气不正常,时冷时热,乡下院子凉,万一感冒了咋办呢?你住在城里大家看望照顾也方便啊。妈妈只说“咦——我还是回去吧,在这我心急得很呀”,义无反顾的样子。说着,她用拳头轻轻砸着心的位置,哀哀地看着我,这下,我再说不出阻止她的理由了。
后来,妈妈特意问我“前几年我和你爸给你拿上去的那棵无花果还在吗?”那是她们用切枝的办法给我从老院的无花果树上嫁接的,爸爸知道我喜欢,千里迢迢,和另一颗合欢树栽到花盆里带到我家。因为家里地方小,枝桠长得太大了,我就放到楼顶养着,后来物业清理楼顶,只好栽到院子的花园里,却被踢球的孩子弄断主干,没有成活。我告诉妈妈那两棵树死了,我没听清她说了什么,我想说其实它们一直长在我心里,但这话说出来好像有点矫情,我想妈妈应该知道我心里想的。
老家有妈妈生活几十年的气息,有爷爷留下的老槐树和老房子,有她和爸爸一砖一瓦为大哥结婚、二哥结婚盖起的房子,有他们拼着老命建起的红砖院墙和体面的大门,有他们精心侍弄过的花园,有熟悉的街坊邻居。她可以在院子里浇花浇树,可以回想和我太爷、爷爷还有爸爸一起度过的日子,可以和老邻居晒着太阳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解闷,不要说那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那也是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家园啊。我没有按照姐姐的意思再挽留她留在城里,我告诉姐姐,不要勉强了,既然老人想回去住就顺着她的心意吧,只要她高兴、健康,心情舒畅就好。
姐姐告诉我,妈妈还是有私心,老向着弟弟,也愿意给弟弟家操劳,看门做饭,毕竟是最小的儿子嘛。家里的老院子也给了弟弟,说不定什么时候“新农村建设”就该征用拆迁了,弟弟弟媳对妈妈态度也不如以前不好了。我不愿意相信这些,老院子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啊,那是我所有关于故乡、童年的美好记忆啊。也许弟弟盼着拆迁会补偿一笔钱,可是我多么不希望老院子有一天会被拆掉啊!
姐姐说陪妈妈回去后村子里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晚上我大哥的小孙女可以陪我妈住,我大哥也可以经常照看,让我不要太担心。她给我从手机里传了一张妈妈在老院子的照片,那是爸爸临终前和妈妈一起种下的木槿花,繁花满枝,开得正好,妈妈站在花下,难以察觉的笑容里透出欣欣然,那是回家的感觉。
妈妈不识字,解放初的妇女扫盲班只教会她认几个简单的字和阿拉伯数字,她唯一能看懂的是“黄历”,能分辨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她不知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千年一叹,但我想此刻她一定心境安详,睡在土炕上,枕着荞皮枕头,即使听着天花板上扑簌簌跑来跑去的老鼠的声音,她也不会再整夜失眠吧。
我因为耳疾听不见电话,但我想知道妈妈回去这一夜还好吗,我对儿子说“今天是母亲节,我只有一个心愿,你帮我给外婆打个电话吧”。很多年前安装电话还需要交纳一笔“初装费”,为了和爸妈联系方便,我好不容易说服给他们安装的电话,算是村里最早的电话了。尽管妈妈搬到城里后家里的电话已经几年没用了,但储存在我手机里那个叫“家”的号码仍会时时浮现眼前,即使我不能接打电话两年多,只能靠发短信沟通了,我也从来没去删掉那个固定电话,那好像是一个永久的印迹。可惜儿子告诉我“查无此号码”,问了姐姐才知道电话早就拆了。
我想妈妈一定是安然的吧。
次日起床打开窗,阴雨瓢泼,气温又下降了,不像五月天,我想着在老院里的妈妈,要戴着草帽、拄着拐棍才能从南面的卧房挪到北面的厨房,湿滑的石阶不会绊倒她吧?但是想到满院缀满雨珠的花树,不管是李树还是杏树,樱桃还是石榴或者葡萄,不管是竹子还是沙枣,还有丁香、木槿、红梅、腊梅、榆叶梅、牡丹、芍药,从夏开到秋的月季……每一棵爸爸妈妈一起辛苦栽下的树,以及爬满院墙的爬山虎,它们有福了,不用等妈妈一瓢一瓢地颠着小脚去给它们浇水了。想着空寂的庭院不会再寂寞地长出荒草,那些花儿不会再开得东倒西歪,我心里说不上是欢喜还是忧伤。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耳朵听不清的日子
听力开始下降的时候,好心的大学同学介绍熟人带我到上海五官科医院专家门诊就诊,一个30来岁圆圆胖胖、油头粉面的男医生看了看我的外耳道,没有受过外伤自然是好的,那为什么听力会下降呢?右边是因为听神经瘤,手术前就听不见了,左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医生斜靠在门上摊摊手,“这很难说的呀,你现在总还可以听见自己说话的吧?”看着他那样无所谓的样子,听着他的油滑腔调简直不像个治病救人医生啊,还是熟人介绍的专家呢。简直是笑话啊,人难道会听不清自己说话吗?那不真变成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吗?我说“现在当然还能听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