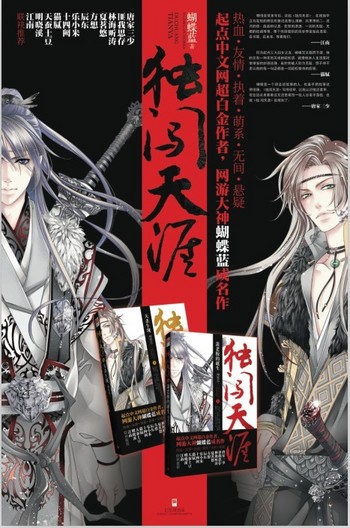�벽����-��8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С�����θպ�������ȴҲ���ҷ�����ֻ����������
�ջ�ֻ�ܶԵ��κܱ�Ǹ��ЦЦ���������׳�����ˬ�ˣ�����Ů�ˣ�����Ҫ��������Ц����
����Ů�ˣ�����������ŵ����漴�ֿ�Ц�����Ѿ���������Ů���ˡ�
����������Ȼ���䣬�������
�ջ��������׳���Ϊʲô��ͻȻ�����ģ���Ϊ�ǵ����Լ�������״����ֻ��������ο���������û�£����ġ���
�������ᣬ��ů�������ģ����������ޱ��顣
����®ɽֲ���������ص����Ŵ���ߵ�һ������������£��������Ĺ��£�������������ձ��˵ķɻ���ը�����ţ������ضϣ������ֻʣ�½��ڵ�ľ��������ȴ��ǿ�ػ��˹����������Ѿ���֦��Ҷï��������Ȼ��
�ջ�վ�����������£����������̵�Ҷ�Ӽ䣬й¶�����ǵ������⣬��֪��ô�����뵽���Լ����׳����İ��飬һ�����Ⱞ���������ش������ܸ�����
�����Ծ���ȥ���׳�����ȴ������Ҳ���ڿ������������ƺ��к���ͬ���ĸп���
�����ǽ�ֲ���ɡ������ε��������ջ�����������ͷ���������ˣ��׳��������ؿ��˻����ı�Ӱ�������˶��������档
ֲ�����滨��ݣ�����ͨ�ģ��ջ��������˵�����������һƬ�����������İ����У�����������������
��ʵ�����ղſ����ģ������Ǹ������е������������������ھ����ش�֮��ֻ������һ����֣����İ��飬����ô����ʮ���֮һ�����ˣ���Ϊ���⣿
����ֲ���������Ϊ�������������٣����Ѿ������IJ����ߣ��ټ��ϸղ��׳���һ��Ҫ����Ϣ�����ָɴ�˳ˮ���ۣ�������˵��������������һ���˴���ظ���
��������ʱ��ҵľ����ֻ����ˣ����Ƿ���վ������˵��һͨ��л�׳��������Ǻ�������л�ջ�����������֮��Ļ�������������Ȼ�����׳���˵��Щ���Ϻ���֮��ij��滰���ֵ��ջ�����ֻ�ǵ͵���ף�����������졣
�����ž�������ƣ��ջ����ֻ�û�������ϵľƱ����׳������ۼ��ֿ�ظ�������һ����ˮ���ջ�ֻ������ؾ��Ű�ˮ���ƣ���������ȥ����Ҷ���֪������˭Ҳû����˼Ϊ������
������۵����ַ���ȥ���ƣ��Ÿ��˷ֳ�����������������������Ǹ����׳������������˿�û��Ȥ��
һȺ��������ɫ���˴��ƣ�������Ȼ�������������ʴ̼���Ц���������ϡ��׳��������ջ������˻ᣬʵ�ڲ�ϲ���������ӵ����գ���ȥ�������ϳ��̡�
ɽ���ҹ�����ó��棬Խ�����������ڵ������Ե÷�������ô�����������Ծ��������ش��зֱ���ջ���Ц�������������˿��̣������۾�����Զ��Ц�ˡ�
�����û�������Լ���������������������Ц�����������������ߡ�
���������˼����̣�ҹ�Ѿ�Խ��Խ�����������������������ȥʱ�Ķ�����߷ֿ㣬����¥ȥ�����Լ������ף����ݺ�һ��������ߵ�������������ϡ�������һ��ij����Ϥ��ζ�����ƺ�Ѭ���������۾����������ʹ����Ŭ����װʲô��û�������������ƣ�������Χ����������Ŀ���Ҫ������û��
��������һ�̣���վ��������Ǹ��Ц�������е����ˣ���ȥ��Ϣ��������˼������
��һ����ǰ���Ȼ��������Ҳ��Ц����û��ϵ�������������Դ������
�ջ�����Щ��������Ҳ����ס���Ͻ��ӳ��Ǹ����䣬�׳����������
���������˶�§���׳��������ֱ��ȥ���Լ�������ţ��ջ����˿�����������������ң�������׳����϶���˵Щʲô��
�����������䲻������ӣ��žͱ������ˣ������ţ��׳�������̺��վ�����棺��ɽ��ҹ�������⼸�����ر����䣬Ҫ��ǵ㡣��
�ջ����Σ��ϴ���˵���ɲ����Բ�Ҫ��ôֱ�ף�
�����׳�����������߶߶�ض�����������Ҫ�ѱ���ͽű߶����ã�˯����ʱ��Ҫ���߱��ӣ���˯��á�����
���ܱ���˯��á��������ջ�������֮���ѿڶ�����˵��ŷ�Ӧ��������ˢ�غ��ˣ�һ�����������ϵ�̺�ӣ��ɿ�ع������š�
�׳��������Ȼ���İ��ĵ�Ӱ����õ�������ǡ�
13��®ɽ����
�ڶ�������İ����������Ϸ壬�׳����ڳ��緹��ʱ���������ջ�˵�����������Dz�ȥ�˰ɡ���
�ջ����ں��࣬һ㶣��������룬��װ��ե�ˣ�����������������ȥ�ɣ��ò����׳���һ�ˣ����ﶼ������ϧ����
������������һ���ܻ��Ļţ�������ȥ��ɽ��
�׳���Ʋ��Ʋ�죬������ȥ�ˡ�
�ȵ����������ʱ���׳�������Ȼ�����������ջ��������Χ���˶��Ѿ����ֲ��֣������ǵ�����׳������ջ�����һ�ԡ������������������Ĵ������ջ����κΣ�ֻ�ܸп��׳���������ŵĹ���֮ǿ��
���Ϸ壬��˵����������������ˣ������ջ��ῴ���������Ǿ��ò���̾�˿���������ʹ��ˣ�û�������ˡ���
վ��һ�Ե��׳����ӿڣ���˭˵�ģ��Ҷ����ó�������
�ջ�����Ƭ�̣��ó������ٵ����ۣ����˼Ҷ�˵��С����С��������ϵ�һ���̶ȣ��ָֻ���С�����������ˡ���
�׳������ᣬ����Ȼ����Ŀ�ŵ�˵���ϣ���Ťͷ����������һ������������Զ����ȴ����������Ц�⡣
����ȻҲ�̲�סЦ�ˣ���ʵ�������������ǰ�Ǹ�ϲ���������Ѿͷ��������������������������졣
�鲻�Խ�������������������ͷ�����ջ��ŵ�һ����������������𣿡�
�׳���Ҳװ��һ������������ͷ���ϵ��˸��棬���Ŷ���Ұ�������������
�ջ���ʱë���Ȼ���۾��ڵ��ϵ����������������
�׳�����Ҳ�ﲻס��������Ц��
�ջ���Ӧ��������ˣ�����������������ص�����
����Ц����������ƻ�����ô������
�ջ�������������һ���������ˡ��׳�����·�߾�������ۺ��Ұ�����ڶ����ϣ������ɵ���Ц��
���������Ϸ壬�ֿ�ʼ��ʯ�Ž����ջ�����Ǽ�ʶ��ʲô�������ڣ�һ�˿���ʯ�ף������͵�ƽ��ɴ�ֱ�ľ�ʮ�Ƚǣ�ֻ��ϸϸ�������䵱����������֮�⣬���ǿ�Ҳ�������¿�����Ԩ��
���λ��ںܾ�ҵ��˵������Ǹ�ɽ���ջ�����û��˼����ֻ����֩����һ������ʯ�ڣ����ĵ����������ߡ�
�����£����ҡ��������Ȼ�����׳������������ջ�����������������̤ʵ������������Ȼ���ͣ���ȴ������ǰ�ǰ㺦�¡�
����̫��������·�����ж���Ϣ��ʱ���ջ������Ѿ����飬���ŵ�ʱ���ƺ������ڶ����׳����������Աߣ��Ӱ����ó������ӣ����ȵ㣬���ơ���
�ջ��ӹ��������־�Ȼ�����ȵ�ţ�̣�����֮���Ǹж���ԭ����������ǰ��ϯ����ȥΪ�����±���ţ�̡�
�����ţ�̣����ź�������ȥ���ƺ�������ů���������������˵����лл�㡣��
�׳���ȴֻ������Ц��������������˵����
��Ϣ��Ƭ���ּ���ǰ�У��������������ڵ��˽��ף��й�������Ϣ��ͤ�ӣ������̵꣬��ҷ��ɵ�����һ���ַ��ָ����ĺ�ˮ�ر��峺��������Ь��ȥˮ��ۏ��
�ջ�Ҳ����ȥ���������������ڣ���������ˮ��ֻ��վ�ڰ�����Ľ���ѵؿ����˴�ˮ�̡�
�׳�������������ǰ��Ц�Ŷ�������֣����ұ����ȥ�����ǿ��ʯͷ�ϡ���
�ջ����ȣ���æ���֣������ò��ã��Ҿ�վ���������
�׳����������ɷ�˵��һ�ѽ�����С��һ�����������DZ����ֵ��˶��������������y�����������ջ������������ˣ�ֻ��������׳���̫çײ��
����·�������ջ��ܿ챻�ŵ�ʯͷ�ϣ��׳���վ��ˮ������������ٺ�Ц����ˮ��մ�������̵Ľ�ë�ϣ���Ө���������������Ƶ�Ц�ݣ���˭Ҳ���������������ջ�������ܿ��ԭ����������������˵������ȥ��ɡ���
�׳������ͷ������ȥ����Ⱥ�˷����Ŵ�ˮ�̡�
���������ѵ÷�������Ŀ��֣����ĵ�̾�˿�����Ϊʲô�������ڣ��������������ۣ�
������Ҫ������Ȫ�ģ�������ɫ����������˵ɽ��������úܼ������Դ��ֻ��ɨ�˵���������ȥ��
�ڷ�����˯��һ���������ջ���������ȥ���ꡣ�׳������ų�����ʱ�����ľ�������һ���龰�������Ů����б���ڻҰ�ʯ���ϣ������ŷ�������꣬������⣬ӳ������������������ƺ�����ë����һ�������������
����Ȼ���̿��ڴ�����һƬ���ף�ֻ�������ſ��ϣ�ĬĬ�ؿ�������
������������ϵ��������䵽��̨��Ե��ˤ�ɰ˰��飬��꾧Ө���ջ����������Ц���׳������Ե�����������̧���۵�ʱ������ײ����������
����������Y�������ջ���Щ����Ȼ�����˾䣺����Ҳ�����˰�����
�����𡣡��׳����߹�ȥ���������Ķ��棬�����˲����Ҷ��ӣ�Ĭ����һ��ȥ���ꡣ
ʣ�µİ�����磬���������жȹ���ż�������ȼһ֧�̣������ջ���Ϥ���Ǹ����ӣ���ζ����ȴ����Ǻ�ǣ���������ĵ���Щ���صĻ��䣬��������������ɢ������ζ���Ļ�����˯�ţ����������߿�����
����������ζ���У������˱��˵ĸо���Ϊʲô���Ǹ�����ô��������ȴ�Ѿ��������Զ��
�׳���Ҳ���֣��ջ��İ������Ѿ����Ǹղ����ְ������������ʣ�����ô�ˣ���
�ջ�ҡҡͷ��Ц��һ�£���û��ô������
�׳���ȴ���еز��������Ц�ݵ���ǿ��������������һЩ����ס�����ļ磬����һ�䣺��������ô�ˣ���
�������ľ��룬�����ϻ����̲�ζ����Ϣ����ǿ�ң���������Ҳ����������ס������Ȼ��ޣ������������֮ǰ���ƿ������ܻ��˷��
���㶵����ţ���û��ȥ�������š������������������������Щ���������ı��ˣ��Լ�Ҳ��Ȼ��Ц��
�������ڵ��龳��������������͵�һ�Σ��ΰ�ļ��ڡ����������죬���ǻ���Ҫ�ص����Ե����������Ҫ�ص����˵Ļ�����
��������ʱ�������˶����Ƶز�˵������������Ϊ���dz����ˣ��������ն���Щ���ơ�
�׳���ֻ����С���뷹���ʹӺ��ų�ȥ���̣������˳���Ӵ����������ʱ����û�����ջ���
��ԥ��Ƭ�̣���������סһ�����ʣ����ջ��أ���
��������ȥ�����ˡ������˻ش��������ջ��ղŴ����ų�ȥ�ˡ�
�������̣��˳�ȥ�������ջ�����Ӱ���Ѿ���Ҫ��ʧ��·�ĹսǴ���
�������˼�������Ҫ������ȴ��û�г�����ֻ��ԶԶ�ظ�������
�����촩��һ�������ѣ�������ʯ��·���������Ƶ��������̵����ӰӰ�´£����������˴�����ġ������
������������Ǹ��϶����Ĺ��
���������߽����ϵ�С�꣬ȥ��ѡ��Щ���İľ�̩�����ӣ�������ѩ����ϸ�������Ź⿴��ɫ�����ϰ��ּۻ��ۡ�
�����������ӣ�����������Ŀ�ĵع䣬��ʱȥ��̷ľ�������ӣ���ʱȥ��ʯ��ʯ������ʱ���ֻ�פ������֯������ǰ��ϸϸ��Ħ�о�������·��
��ʼ�ո��ں��棬���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