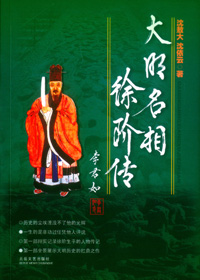大明首辅-第2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是萧墨轩可是从“市场经济”过来的人,当年那篇《多收了三五斗》更是曾经背滚瓜烂熟。
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便就传出官府和织造坊要照平价收购粮食和丝绸的消息。那些本想廉价出售收获的百姓,得了这个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直接便捂紧了口袋,宁可多赶上几十里的路去府城里卖,也再不肯廉价。
那些商人和大户原还是有些不信,可眼瞅着官府和织造坊还真的就拿出了银子来买,也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了事实。
几回折算下来,直浙两省官府共收购粮食六十六万石,折合现银三十三万两。江南织造局在南京,杭州和苏州的三处作坊,共收购棉花九十万斤,折合现银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收购生丝三万两千斤,折合现银六万六千两。总共花去了大约是五十万两出头。
再分成两季,每季也不过是二十多万两银子的花消,对于直浙两省来说,抄出家底,也并非什么太难的事儿。可银子花下去,当年直浙两省的物价竟是没生什么大的变化。
原本就是丰年,让人欢喜,又有官府稳定了物价,两省百姓鼓腹歌。私自底下,竞相称萧墨轩为“萧青天”。
只是……当他们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其实萧大人也正笑嘻嘻的数着银子。
平日里边,直浙两省除去盐铁等税,每年里头能收上来的税折算下来,也只有一百二三十万两地样子。即便是遇见丰年,也不过能多个半成。究其原因,其实也就是常收的人口税仍是不变,而市场上头的营业税,百中取五。可东西掉价了,多收也多不出多少来。
可今年不一样了……东西居然没掉价,营业税虽仍是百中取五。东西多了,税收自然也就多了。计算下来,今年的税银子竟是多收上了两成,足有一百五十万两之多。
虽是买入货物花去了不少,可买来的东西并不会浪费,自然会有用处,只那些生丝和棉花,做成了丝绸和花布,又可以折价抵上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新开的海贸也少不得这些东西。官仓里的粮食多了更是不用犯愁。用处多着呢。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从湖广购买的木材。想是这几日便可以运到南京。
这些木材一部分是用来建造兵船的,另外一部分则是用来制造货船。
在这之前,大明地兵船和货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或者说,两者兼可通之。
可加上了侧舷炮和增加了更多水密舱的兵船,却是很难再完全互通。不过这边增加的成本,萧大人倒也不担心。
合营,合营,那些南直隶和浙江的大户们既然上了合营的船,难道市舶司造船你们还想少掏银子不成?其实这也是萧墨轩在想想。那些大户掏银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过一丝犹豫。
沾了朝廷的光,在龙江船坞造船居然是不要工钱的,这样一来在成本上也降低了许多。再加上这几个月来。他们确实也尝到了些甜头,更不用像从前那般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也是开怀。
还有一件令萧墨轩乐着地事儿。便是经略府里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便就是萧墨轩的老相识,徐渭。
萧墨轩确实没有欺骗徐渭,胡宗宪在京里被折腾了几回,竟是渐渐得没人注意起他来。毕竟连严嵩都已经倒了,严世蕃都已经授首了,还折腾个胡宗宪还有什么意思?面对一个已经几乎丧失了反抗能力地人,这样打发时间都显得无聊。寻了个机会,由大理寺上了封疏,只说胡宗宪并无过失,圣恩之下,胡宗宪开释回乡。
胡宗宪的老家徽州绩溪(好象是个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大人物),也属着南直隶。
从水路回乡途中,胡宗宪也听说了徐大先生自杀未遂的事儿,顺路弯去了绍兴探视。两下嘘唏一番,竟都是对萧墨轩心存感激。
“胡大人且还是不愿见我?”萧墨轩端起茶杯略泯了一口,对着徐渭开口问道。
自从徐渭来了经略府里,做了萧墨轩的师爷,这几日来萧墨轩最明显的感觉,便是轻松了许多。
徐渭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虽是科举不如意,但是治政谋军,确实有一手。
隐隐间,萧墨轩甚至觉得此人才学堪比当年的“卧龙”,“凤雏”。让这两人来考科举,其实也不一定能考得上呢。
“人各有志,萧大人何必强求。”徐渭讪笑一声,轻轻个摇了摇头。
“他莫不是怪我……”萧墨轩捏了捏指结,“朝廷里的事儿……
“萧大人想做大事,绊脚的自然要踢开。”徐渭似乎比萧墨轩看得还要清明,“萧大人又何必在意,若要在意,也是在为国为民上头。”
“文长并不是要和萧大人说大道理。”徐渭抬起眼来,只见着萧墨轩有些愣愣地看着自个,微微一笑,“日后这如何评价,却还在天下人的口中,并不是改一两封书,便是变得了的。”
“哦。”萧墨轩听了徐渭的话,呵呵一笑,抬起手来作了个揖,“今个听了徐先生地话,当真是受教了。”
“萧大人天资聪慧,博文广记,难得又兼宅心仁厚,心有大志,徐某也好生敬重。”徐渭点头道,“若不是如此,徐某也不会坐在这里。”
—
徐渭说的这番话。像是在夸萧墨轩,其实却也颇有些清傲的感觉。只是萧墨轩素知他们这些文士地脾性,哪里会去和他计较。
“可胡大人毕竟是受了严嵩的恩。”徐渭说了一半,突然又话锋一转,“这其中恩怨,只当路人偶遇便是。”
“唉……”萧墨轩微叹一口气,点了点头。
“萧大人。”正说着话,一名承宣布政使司地佥事,站在门外轻轻唤了一声。
“嗯?”萧墨轩朝着门外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进来说话。
“萧大人。从湖南购买的木材,适才已经在江边的码头上边靠了岸。”那佥事小心的回道,“布政使刘大人派卑职来请问萧大人,可是要去亲自查验?”
“哦,这便就已经到了?”萧墨轩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来,“原本只当是还要再过几日。”
“刘大人可是派人查验过了?”萧墨轩问道。
“这是自然。”那佥事点头回道,“萧大人您早就吩咐过,这是紧要的大事,刘大人和卑职们又岂敢怠慢。”
“既是查验过了。那倒也不定要去了。”萧墨轩也是点了点头,“点清了数目。直接按着配好的份额分送到两座船厂里头便是。”
“哎……”那佥事应了一声,就要转头退下。
“慢着。”萧墨轩未及他离开,突然又出声叫住。
“萧大人还有如何吩咐?”那佥事立刻站定了转回过身来。
“最后究竟是用去了多少银子?”萧墨轩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倒了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反倒是满打细算了。
“哦。”那佥事连忙回道,“今个且是先到了十七条船,每船载八百料,共需银三万零六百两。还有四五十条船,也都在年前到。”
“三万零六百两?”萧墨轩心里略一计较,却突然脸色一变。“把木料的银子和每船一百两的车船人夫地花消全算上去,至多也不过两万八千九百两,缘何又多出了一千七百两?难道这一条船上的木头,途中竟是要花去两百两不成?”
“大人误会了。”耳听着萧墨轩语气似乎有些不对。那佥事也吓了一跳,“卑职们断不敢欺骗大人,只是适才大人没问。卑职也不好说。”
“那多出来的一千七百两,却是船只经过江西的时候,被江西河道衙门收去了每船一百两的税。”佥事回道。
“税?”萧墨轩顿时不由得一愣,“能装八百料的船,自然是大船,何必在他江西境内的码头上靠岸补给,又不入他江西的内河,如何会被收去了钞关税?”
“这……”佥事见萧墨轩问起这个,也是有些哭笑不得,“小的也不尽明,可是据说,他们收的不是钞关税,却是什么‘过江税’,江西河道衙门里地船,只在江面上拦住,不缴却不放行。大人若是想要知道得仔细,须得去问随行之人才是。”
“过江税……”萧墨轩想了好一会儿,似乎也没想起来还有这么个税,抬起头来,有些纳闷的继续问道,“可是给他们看过公文,说过这也是官府地采买?”
“自然是说过了。”佥事苦着脸回道,“可他们说,只认得朝廷和他们省里的公文,若是军部得,也算得。其他的,便是不必看了。”
“荒唐……这且是和强盗有如何区别?”萧墨轩这才算是彻底明白了过来,自个是给别人“打劫”了,一下子便就上了火。
“这些个贪官,且还有没有了王法。”萧墨轩腾得一下站了起来,愤愤的来回走着,挥着衣袖,“难道他们竟是以为本经略就拿他们没了办法?朝廷里边,我且还是可以参他们一本。”
发了一通火,转回头来,却见徐先生只是坐在那里,笑眯眯的看着自个,萧墨轩顿时也觉得有些失态。连忙坐了回去。
“其实萧大人也不必恼怒。”徐渭呵呵笑道,“此事历来如此,只也算是劫富济贫罢了。”呃……劫富济贫,萧墨轩有些好奇的看着徐渭。
第九章 目光
江西一省,与邻近的湖广和直浙诸省相较,差之颇远相似。”徐渭见萧墨轩如此好奇,开口笑道,“常年里头,地方上的赋税都是难收。”
“故而每当有来往于江浙与湖广之间的货船,每每会多收上过路费。”徐渭口里说着,面上似乎也有些无奈,“虽是有些无理,可是倒也算是减了一地百姓的负担,倒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
“若是如此说来……”萧墨轩愕然的张了张嘴,竟似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是低下头来,轻轻摇了几下。
屋里的两面火盆,把公房里的空气烤得有些干燥。
萧墨轩缓缓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寒风呼啸而入,迎面吹在萧墨轩的脸上,让人清醒了许多。
南京的冬天和北京略有些不同,北京的冬天虽然温度更低些,可是却是干冷,风吹在人身上叫做“刮面”,而南京的冬天则湿气重了许多,寒气直逼到人的骨头里边,叫做“刮骨”。
不过好在萧墨轩对于江南的气候,倒也十分适应。摸了摸衣袖,里头放着上个月爹爹从京城送来的家书。
信笺里头,其实倒也没说什么,只是念着天冷了,要多加几件衣裳,夜里睡觉的时候,褥被窝紧一些。顺道又叮嘱了几句,须得小心照顾好自个的家眷……尤其是苏儿。
离年三十没多少时候了,兴许,今年的除夕真的要在南京过了吧。萧墨轩的嘴角微微动了几下,心里头像是缺了块什么似的。
“家书一封抵万金。”眼下虽然是太平之世,可是又如何能隔舍得下这份心思。
信中虽是没提及娘亲和岳母。可是她们岂又能少得了牵挂,萧墨轩默默闭上眼睛,任一丝暖流在心头滑动。
“萧大人。”这一声,并不是从公房内传出来地。萧墨轩微微睁开眼睛,却见是一个站在窗前的杂役。
这杂役想是原本想来公房里头禀报事情的,却看见经略大人站在窗前,连忙先敬了一声。
“嗯。”萧墨轩点了点头,看着那杂役转过了窗前,走了进来。
“萧大人,浙江海道王副总兵说有急事求见?”。着头。朝萧墨轩报道。
“哦,王浚?”萧墨轩连忙移了几步,转回到案桌前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