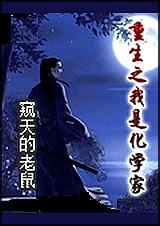和尚与哲学家-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续存在下去。经典的例子就是一杯水,它被一条鱼感知为栖息处,被一个人感知为一种饮料,被一个神灵感知为一种具有不死性的美酒,被一个精神受到贪欲折磨的世俗之人感知为血与脓,被一个将世界看成地狱的人感受为液态的铜。一首掸诗也说道:“对于情人来说,一个美妇人是令人欢喜的对象;对于隐修士来说,却是一个引人分心的物体;而对于狼来说,则是一顿好饭。”我们的感受,尽管是由客体启动的,最终还是心理的产物(elaboration)。当人们看到一座山时,来到我们心中的第一个意象是一种未被制作的纯感受。但是下一个时刻,有人会对自己说:“噢!这座山看上去危险,不友善。”另一些人会对自己说:“这正是个能建一所隐修院的好地方。”然后,许多思想相继而来。如果客体自己来给自己下定义,并拥有一些不取决于观察它们的主体的固有品质,则所有的人都应该以同一种手段感知它们。
让—弗朗索瓦——这些分析非常正确,但我要重复我说过的话,这些分析对于一个哲学家也是经典的。可是,我们说,它们又是怎样与一种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智慧连接在一起的呢?
马蒂厄——如果我们以沉思的和分析的方式分析我们的感受,我们最终将会不再眷恋于这些感受的牢固性。人们理解一些如“朋友”、“敌人”之类的概念的短暂相对性——我们今天感知为敌人的某个人对于别的一些人则是一种巨大的爱的对象,而我们也许会在几个月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通过精神锻炼,使我们对人、对事物的判断和感受的牢固性融化,就像我们使一块冰融在水中一样。冰和水是同一种元素。但前者是坚硬的,人们能在上面撞断自己的骨头;后者是软的、流体的。因此人们能将整个世界感知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将它分成“可欲求的”和“不可欲求的”;或者相反,将它感知为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丧失了自身存在的转变活动。人们甚至能够在众多现象之中认识到一种与空同义的、无限的纯。这当然创造出一种巨大的差别。
让—弗朗索瓦——对于现实,对于总体的人类,这里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伊壁鸠鲁学派、佛教和斯多葛学派所共有的。其意思是说,世界的现实和人类就本身而言,其整体是不能被改善的。能够被改善的,惟有人类的心理。解决的方案最终就是达到精神性,达到个人的智慧。且说说我最熟悉的东西,伊壁鸠鲁学派或斯多葛学派哲人,乃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我越是不介入这个世界的所有纠纷之中,任众人的愚蠢行为与我毫不相干地发生,我就越是能够为自己安放好车辆,以使用一种大众的表情,越能够不置身于有可能扰乱我的磨难之中……我尤其要避免对自己说我能改变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我所能改变的仅是我的行为表现和对于这些环境的思想。尤其不要为某一方、为某一事物辩护……”与这种态度相反的是另一种态度,它意思是说:“不,我们可以改造现实。我们可以改善它,我们可以对它有所作用。因此,哲学的目标不是控制我们的思想,使之不能参加到任何的客观形势之中,而是要以技术和政治来改造这种客观形势。”柏拉图曾试图将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
马蒂厄——我相信佛教也提议这两种态度的联姻,但这是一种建立在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联姻,我觉得这些原则一方面比不干预、另一方面比技术和政治的使用都更为本质。首先,不需要改造现实自身,我们不妨说这是事物的最终本质,因为,根据佛教的说法,事物的完善,也就是原始的纯洁性,既不在人们不知它时而被“降级”,也不在人们认识它时而被“改善”。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改变的,乃是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错误感知。正是在这种改造的范围内,对思想的控制和意在向他人提供实现这一改造的方法的利他主义行动在起作用。佛教的道路最终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新感知,一种对人身及各种现象的真实本质的重新发现。它使得人们能够更加不易为生存中的偶然事件所伤害。因为人们将懂得不仅带着“哲学”,而且还带着欣喜去接受它们,并且将困难和成功都当成能使人在精神实践中飞速进步的催化物来加以利用。这并不是要将世界与自己隔绝,而是要理解世界的本质。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目光从痛苦上移开,而是找寻治疗方法,并且超越痛苦。
让—弗朗索瓦——哪种治疗方法?
马蒂厄——每一个存在者自身都拥有成为佛陀,也就是达到彻底的解放和认识的可能性。只是一些外来的短暂的幕蒙蔽了这种潜能,阻止它表现出来。人们称这些幕为“无知”或“心灵的昏暗”。精神的道路即是要将自己从各种消极情绪、从无知中解放出来,并通过解放而使这种已经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完善(Perfection)变为现实。这个目的没有丝毫个人主义的成分。将我们引上精神道路的动机乃是改造我们自己,以便能够帮助他人从痛苦中自我解放。这种利他主义的观点首先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他人痛苦时的无能,接着它产生出我们为救治他人痛苦而进行自我完善的欲望。所以这不是一种对世界的漠不关心。面对外部环境的坚强(invulnerabilite)成为一件甲胄,人们披着它投入与他人的痛苦进行的战斗中。
让—弗朗索瓦——在提交给哈佛讨论会的报告中,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达尼埃尔·戈尔曼在其报告的开头称:“在哈佛进行了一些心理学的研究之后,我曾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收获,即心理学是一种在欧洲和美洲起源的、于上个世纪在这两个大陆上——也就是在西方——诞生的科学题目。”……这里,我想要提醒人们,在希腊哲学中有一种心理学……说到底!……他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人们所理解的意义上谈科学心理学的……然而他说,当他开始到亚洲旅行时,他发现在那里,尤其是在佛教中,存在着一种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的、非常发达的心理科学,回想起来,他感到惊愕,因为看到他的西方心理学方面的教授们从来也没有表示过要像讲授西方心理学学派一样地讲授这些心理学学派。这也就意味着在东方存在着一种根据人们在西方所称的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定义的心理学——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种心理学充分符合“科学”这个名称,除了在其神经生理学的部分。但有个职业心理学者对我们说,对于心理过程的各种现象所进行的科学的冷淡(detache)观察,并不是严格西方式的。很久以前就有这种研究,特别是在佛教中。
马蒂厄——不妨顺便说说,戈尔曼并不是惟一为这种对东方学说的缺乏兴趣而感震惊的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成员、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也写道:“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史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renaissance),其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我们哲学的现代历史对于印度思想一无所知,它是不自然的,因为印度和希腊不仅与我们共享着印欧语言遗产,还共享着许多文化的和哲学的忧虑。”
让—弗朗索瓦——那么,佛教的这些应该说是不拘束于一种个人改善和获得安宁的理想、而专心于精神和心理过程的单纯研究的心理学研究,包含了什么?
马蒂厄——我要举一个与对感知的研究有关的简单例子,因为这种研究是对心理功能所作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当人感知一个对象时,即使是最简单的对象,比方说一个蓝方块,人们可以区分这方块的表面、角、边等等。这众多因素被综合地感知为一个方块。是有一种对于对象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的瞬间的、总的感知呢?还是由对于客体形成一幅综合图像的每个细节的意识的那些短暂瞬间组成的一种快速连续?恰如当人们伸直手臂快速地转一支火把,人们看到有一个火圈,然而,这其实只是对一个处在连续运动中的光点的众多感知。在佛教文学里,存在着一系列这类分析,一些多达数百页的论文就是针对这些现象的。
让—弗朗索瓦——它们是何时写的?
马蒂厄——从耶稣基督前六个世纪的佛陀的言语,直到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出现了许多为有关感知的文献作注的伟大的西藏注经者。人们还在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以生动的方式分析它们,同时,几乎每天在我们各个寺院中都举行形而上学的辩论。
让—弗朗索瓦——那么,这很有趣,因为这酷似一个心理学学派,它曾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派之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完形心理学说,即Gestalt Psychologie①,它于二十世纪初诞生,并在一本光辉的书中被出口到法国。作者为我在索尔邦大学曾师从过的教授保罗·纪尧姆。他在五十多年前写了一本书,名为《完形心理学》,这本书今天依然流行。这真是在写作上清晰和准确的楷模。完形心理学派产生于如下的证明:心理学就实质而言,一直到现在,都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一直相信我们对客体的感知是一种由这些客体的每一个构成因素开始的建筑。我们认为是一点一点地到达最终的完整的客体,而事实上,真正的过程——完形心理学起源于在实验室中进行体验时的试验方法——乃是我们一下子感知综合的整体(ensembles synthetiques)。有关“复杂性”和“自行组织”概念的认识科学的最新理论也以能够与这种佛教分析相对照的术语提出了总体感受这个问题。完形心理学自身已受到了质疑,然而,这是一个还在耶稣基督前六百年就被佛教在对感知的研究中,以几乎相同的术语提出过的问题。
①德文:完形心理学,或音译为格式塔心理学。
马蒂厄——没有任何客体是持久的,事物细微的非持久性体现在,每时每刻客体都在变化。由于意识是被客体启动的,那么,非持久的客体有多少状态,意识就有多少瞬间。这种对现象和思想的瞬间非持久性的概念,走得很远,因为它显示,如果在现象世界里存在着,即使是惟一的一个固定、持久、固有地存在的实体,意识就将仍然是如同“贴”在这个客体上一样,并且会不限定地持续下去。最终,世界上所有的意识都会发现自己几乎是被这个客体“捕获了”,它们无法摆脱这个客体。正是这种细微的、非持久性的出现引导佛教将现象世界比作一场梦或一个幻象,比作一条变化着的不可把握的流。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牢固的事物,比方说一张桌子,也在每时每刻变化着。思想的流也同样是由被外部世界的每一个这种极细小变化所启动的无数极细小瞬间构成的。这些瞬间的综合才能给人一个粗浅的实在性(realite grossiere)的映象。
让—弗朗索瓦——这个看法与一种非常重要的柏拉图式思想正相反。在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那里,尤其是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找到这种思想——我甚至要说这种魔鬼附身的顽念(obsession)——即我们不能认识动的事物,改变着的事物。对于他们来说,现象(Phenom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