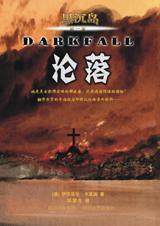梦回新雪季-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梦回新雪季》目录
一、归来…001
二、珠江加油站… 003
三、九号道… 007
四、二锅盔的野雪… 018
五、滑雪的理由… 030
六、偶像走了… 042
七、夜雪… 056
八、向北走… 065
九、木刻楞… 084
十、必须的飞越… 108
十一、山谷… 121
十二、雪中之火… 136
十三、西伯利亚的车辙… 152
十四、四年后… 165
十五、两封电子邮件… 174
本没想写的后记… 176
当凌厉的板刃划过坚硬的冷空气,狂舞的雪雾被恣意加速的血液融成水滴甩在癫狂的雪板后面……久违的山风回来了,铺天盖地的鼓声回来了,死去的童年回来了。
嘿,走嘞!
。 想看书来
一 归来
正午,我坐在亚布力六号道和九号道的交点,也就是九号道的起点,看着早春的雪道和早春的白桦林。这大约是二○○八至二○○九雪季的最后一天。
沉重的雪鞋沾满湿软的雪。身下的雪坡很暖。
终于,我站起来,踩上雪板。
我可以对自己没交代,但不能对朋友和家人没交代……曾经给我的生命以豪壮并承载我和她联袂疾飞的九号道,你似乎可以是我最后的交代。
我要直滑下去,不做一下回转,把肢体和生命交给老天。
嗬,老天,我倒要最后再领教一下你究竟能对我背叛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侥幸成功了,说明你还并没有抛弃我。
卢芳告诉过我,在这样的陡坡,这副一百七十厘米的雪板能给我这七十五公斤的体重带来一百一十公里以上的自然速度……出发吧。再见六号道,再见卢芳。
出发前我必须回头看一眼。卢芳当然不会来,但我必须看一眼——因为要说再见。雪坡上方没有一个人滑下。
出发吧。
“薛乾!”
梦中的声音在喊。在身后。
分明,但我知道那是幻觉。
还是不要耽误了出发。
“是薛乾吧。”梦中的声音真真切切,我不由得回过头。
是她。
后来她说她一直站在我的身后,坡下那一侧。她还说,从一开始她就看出我憔悴得不成样子。
她当时像五分钟前才分别似的说:“嗨,先下六号道吧!”
这就是我们的重逢。
二 珠江加油站
每个人都有故事,能讲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却很少。
多数成年人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值得或不方便讲出来。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人,但我却打算把我二○○五年至二○○九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值得,也没有任何不方便。
因为那几乎是我唯一值得讲的故事。
写这故事时,我在满洲里以北五十公里的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区,在我那仍然寂静的厂子里。这儿的冬天出奇地漫长,我需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春天的来临。我坐在从国内带去的那把旧椅子上,从容地等待春天,从容地写完了我的——不,是我们俩的故事。
二○○五年二月十日,大年初二,我和邱实开着我的那台旧捷达去亚布力。过了玉泉开始下雪,到珠江加油站时雪已经很大。我就在这里遇见了她。
那时的哈牡路还是高等级公路,珠江加油站就在通往亚布力滑雪场的路口对面。我下车加油,邱实去找厕所。
大雪弥望,看不清四周的山势,更找不见雪道在哪儿,连林海都被雪的帷幔遮得若隐若现。眼前这景色在沈阳绝对看不到,那里只会看到黄草灰树之间的若干条人造雪道。无数次听人说起过这儿,也许是因为这场大雪,现场的景致超出了别人的描述和我的预期。
“对不起,能打扰您一下吗?”身后有一个女声说。
我回过头。是两个年龄和身材都差不多的姑娘,说话的穿着红色滑雪服,扎着马尾辫。
“您是去雪场吗?”
“是啊。”我说。
“我们的车坏了,能搭您的车吗?”她边说边指了指旁边的一台紫色切诺基。
“没问题,就你们两个人吗?”我问。边看了一眼她身后那位留着齐耳短发的。
脚下的雪地忽然变得很热。
“还有一套雪具。”
短发回答。她穿一件白色短款羽绒服,系着一条深棕色粗线围巾。在礼貌的时限内,我只来得及看清她那很浓的眉毛及这眉毛下因雪絮而眯缝起的双眼。
“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短发又补充了一句。
邱实回来,用夸张的东北话说:“都是老乡,客气啥呀!”边说边去那切诺基里拿雪具。转身前还用一只眼睛冲我眨了一下。和女孩打交道,他是行家。
马尾辫说她们有急事,必须在中午前赶到雪场。
加油的丫头喊:“一百一十二!”
我俯身去车里拿钱包。当我取出钱时,发现短发已经把钱付了。
没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举动,我说:“这——”
旁边邱实说:“您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成了跑出租的了?再说跑出租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呀!”
“不不,你们千万不要误会。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经理答应给我报销两箱汽油。我的车有一箱也就够了,我想用另外一箱交朋友。”短发蹙了一下鼻子,很调皮地笑。她小巧的鼻子很漂亮。
“谢谢。不过,接受了您的这箱油我可就不仗义了,您不会让我犯错误吧。”我说。并把加油女孩手里的钱还给短发。
“必须吗?”短发盯着我问。
“必须。”我说。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些生硬,便又追加了一句,“ 哈,其实我也能报销。”
马尾辫过来拽了拽短发,说:“那就算了吧。”从表情上看,她也没想到短发会有这样的举动。
车上,四个人各自做了介绍。马尾辫叫崔冰洁,短发叫卢芳。
崔冰洁递了名片。那上面印着——亚布力滑雪学校副校长。
“亚布力是个风云际会之地,所以我不敢说在技术方面能给二位做指导。不过,如果有事需要帮忙我随叫随到。”崔冰洁说。
“哈,校长,多亏没收你们的油钱!”邱实很兴奋。他雪滑得好,上学时在沈阳的高校赛中拿过冠军,后来还在全国大众高山赛中得过名次。人长得亦帅,其几任女友差不多都是滑为媒搞上的。
卢芳一直没说话。她坐在我身后。
可她显然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明摆着,她不想欠两个陌生人的情。或者还可以这样理解:她在提示我们,别指望把相助的举动当成非分之想的资本。
这么想着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感觉她在盯着我的后脑看。
三 九号道(1)
陈雪覆盖的路面上新雪已经很厚了,车子多次打滑。进景区时已近中午。崔校长和卢芳直接去了雪场。雪还挺大,但缆车并没有停。我和邱实先办了酒店入住,之后顾不得吃饭,扛着雪板奔雪场。
上缆车之前我们让人以雪道为背景照了张相。之后我转过身,看那雪中的山和雪道。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本溪关门山的姥爷家,那里靠近深山。从记事开始,我便有一个奇妙的感应:每当仰头望大山,耳朵里便会响起咚咚的鼓声。山越高、林越密,鼓声越沉重、越清晰。这是我的秘密。我一直相信那鼓点中有一个古老而遥远的声音在召唤我。
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山林,去主动接收那鼓声。这没有直观理由的举动让我上瘾,一直到大学毕业,几乎每一个假期我都会去钻山。我这“钻”有别于时尚的徒步和登顶——我躲开一切景点、线路和游人,随意在某个心仪的无名山前下车,然后就在那一带流连,直到吃光干粮。没遇过危险,因为我从未尝试深入。国内所有省份差不多都去过了。很遗憾,一直什么都没听懂。人却越来越孤独,孤独中糊里糊涂地过了而立之年……从未疲倦过,直到最近。
曾经带何泓在海螺沟的一处原生态温泉旁搭帐篷,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整整两天。帐篷坏了……何泓发誓说再也不会跟我出来受罪。她是个说到做到的女孩。
邱实屡次怂恿我去滑雪,说光钻山沟子有啥意思,世界上还有一种最好玩的游戏你没尝试过呢。我最终尝试了,发现他说得没错,还发现山林中的滑雪场可以对抗孤独……便在有雪的日子里用滑雪取代钻山。
我仰头看雪中的山和雪道,等待鼓声响起。
“嘿,醒醒吧哥们儿!再磨蹭太阳都该落山啦。”邱实喊。
鼓声并没有响。是没来得及还是我的耳朵变得迟钝?
这个叫做三锅盔的山上有茂密的松柏、灌木和白桦,五六条高山雪道在林木中垂下。滑雪的人并不多,很好。视野差一些,但足够用。
雪道很长,吊椅式缆车很慢,上山用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缆车上,邱实问我:“你说人在吃饱穿暖之后为什么要滑雪呢?”
这种情况很少见。关于滑雪,从来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并且,这问题似乎太深沉。
“是啊,这是个问题。”我说。
下面有一对单板滑下去,很流畅,听不到通常的扑哧扑哧的减速刻雪声。女的尽兴地尖叫,她那紫色头盔上有一个很大的白圈儿。
“就为了喊这一嗓子。”我说。
“这几个字够简洁。”邱实说。听口气,他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
“别忘了,晚上把老二要的稿子给写喽。”他说。
他弟弟在一家户外杂志当主任,让我写一篇滑雪的感受。
快下缆车时我才发现邱实用的是长板,这更少见。通常,初到一个新雪场,我们都是先用短板,这是安全的选择——短板滑小回转更容易控制速度。
“咋先上长板了?”我问。缆车站到了。
“下去再告诉你吧。”
三锅盔顶峰是四条高山道的起点,从难到易依次是九、八、七、六。我想按惯例先滑号称幸福大道的六号道,邱实说你怎么越来越讲究了?走,非九号道不滑!
小子今天有点怪。
九号道很陡,站在起点往下望,脚心都有痒痒的失重的感觉。我做深呼吸——每次面对新的陡坡我都会这样,这是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滑雪所能带来的所有快乐的一部分。
三 九号道(2)
这儿肯定昨天就开始下雪了,并且起码昨晚没有轧雪——雪道上的暄雪很厚,像野雪一样被雪板推得坑坑洼洼,滑惯了硬雪的人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望不见雪道的尽头,不断有人从身边滑下去。 蓦地,休眠了一年的豪情自胸腔升腾,山林的鼓声也如约而至!哈,你终于来了。
扣上雪镜,戴好护脸儿,攥紧雪杖,开始吧。
我其实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急于把一年来的委屈向雪道诉说。
邱实先喊了声“走嘞!”冲了下去,我随后滑下。
一旦耳边响起呼啸的风,对坡度的恐惧便即刻消失。速度来了,血涌上来了,天上的大雪不见了,两侧的树林也不见了,见到的只有扑面而来的雪道。
我先得客观地描述一下我们那天的第一滑。
邱实不够完美,前两个回转没有适应好暄雪的阻力,打了趔趄,但也仅此而已,身经百战的他很快调整了动作,顺利滑完后面的行程。但坦率地讲滑得不够从容,没有以往那么潇洒,感觉像是急着赶到终点。以往,他追求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