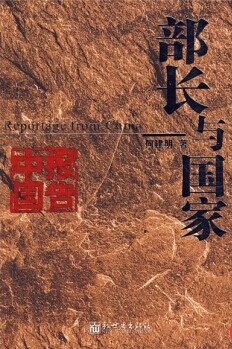祈愿者-魅步杀伐-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越是放不下更忘不了,那样的狂躁和痴心,直直要将她的人连同一颗心生生绞碎。
表哥,如何……才可以?
屋外,卉珍守在廊子下,心不在焉的拨弄着新摘下制茶的花儿,翻过来,又翻过去,心中烦躁,怎的还不干。
抬头偷偷看去,屋内,溪兰额间的金钿花上透亮地反射起清澈的水光,比寻常的花钿要柔亮许多。空气里全是溪兰的气味。卉珍嗅着溪兰身上初闻异常清新柔美,再闻却是止不住风情缱绻的香,想象着终有一天那人将如痴如狂的模样,不由微微红了脸,连脚都酥软了几分,颤颤扫溪兰对面正饮茶的巯正一眼,少年英俊,却不是自己能亲近得起的,一丝嫉妒一丝忿恨。
……………………………
屋外,卉珍守在廊子下,心不在焉的拨弄着新摘下制茶的花儿,翻过来,又翻过去,心中烦躁,怎的还不干。
抬头偷偷看去,屋内,溪兰额间的金钿花上透亮地反射起清澈的水光,比寻常的花钿要柔亮许多。空气里全是溪兰的气味。卉珍嗅着溪兰身上初闻异常清新柔美,再闻却是止不住风情缱绻的香,想象着终有一天那人将如痴如狂的模样,不由微微红了脸,连脚都酥软了几分,颤颤扫溪兰对面正饮茶的巯正一眼,少年英俊,却不是自己能亲近得起的,一丝嫉妒一丝忿恨。
大湘叹了口气,自从病好,小姐变了一个人,不只人变了个样憔悴许多,性子也变了。往日里爱花不假,如今更是每日里要大把的花,摘来却再美的也不赏,就坐在床边一把把扯下花瓣,那眼神越来越古怪,看得大湘阵阵发麻,每次都没忍住那阵阵寒意。而且小姐再不要大湘梳发挽髻理鬓,也闲了首饰香油,空着妆奁箱笼,只选些白玉首饰,还不肯多戴了,衣饰也只捡些不太艳色的,全身连个香囊也不配,只戴了那只辉蓝玉双鲤戏珠佩,莹莹光洁。
只是她仍用了白玉胭脂盒子的“娇娘”胭脂,那光艳四溅的唇膏子。略显苍白的脸,配上黑夜一般的发和那如刻印一般深深印在大湘脑海里的红,让大湘每每惊愣非常,多久也不能习惯。
深夜,沐浴后的顺和轻轻坐在妆台前,静静凝视着镜子里的倒影。良久起身,将大湘提来的花篮拿过来,轻轻用指腹扫过那些娇艳的花儿,眼里一片空茫。突然眼里一闪,狠厉地抓起来一把把将花揉下,全然不管花枝粗砾会伤了柔荑,一时屋内飘起香艳颓唐的气息,花瓣如雨如泪,洒落在妆台上、地上。
残枝满地,红香碎败。
眼前浮现起那日偷偷见到的情景,花园里凉亭中,无风,娇语阵阵,笑靥妖娆,身旁的分明是她心上最在意的人,玉簪丝履,衣带翩翩。心惊,心乱,心寂,痛到无泪可流,分明是把钢刷,刷得全身全无一块好肉。那波光水色,那杏花纷飞,那轻舟荡漾,那金堂玉马都再进不了她的眼,那一刻就是她的终点,再没有什么于家、季家、再没有什么过去以后。
她恨。
我如何能在那个冰冷的府里度过孤苦的一生?
如何行尸走肉般活下去?
如何能把对你的执念消融心如死水?
嬉笑声传过来扯动了她的神经,震得细碎的紫色花瓣无声的落下,直落在顺和发上、脸上,纷纷如下了一场花雨。她就那样呆呆看着远处,一动不动,脸上那不敢相信的哀伤表情仿佛落下的不是一场花雨,而是她的心碎裂的一场华丽落幕。眼泪无声息就下来了,冰凉的爬在她姣好的脸上,弯成了悲哀的曲线,如河流般无情将脸上的花瓣带落在泥里。
喀嚓,嗤,咚咚……
轻微的怪异的声音随着那如波汹涌的愤怒在夜里传向外间浓浓黑雾笼罩的一切,却在碰触到那诡异的黑雾的时候,被无声却又异常凶狠的反弹回去,不叫半星的异样外泄出去。而那古怪的声音仿佛是有生命的魂灵,一次次被挡回,有一次次冲向那浓黑,化作了尖利的嚎叫,瞬间消失无影。
房间里,豆大暗黄的灯芯在那华丽的鎏金刻花铜灯盏里摇摆身姿,照映出扭曲的影子,张狂的铺张在墙上,屋里,无处不在。
喀嚓,顺和一剪刀下去,咔嗤,又一剪刀,发,美丽如云的发,被她一缕缕剪将下来,在桌子上堆成了一小堆。还在剪,继续剪。然后抓拢起那曾经无比爱护的东西放进一个古朴粗糙的乌木瓶子里,再抓起一把小石杵,狠狠的捣着。那头残发参差不齐,微微散开如同从前那丧夫疯癫的妇人,张牙舞爪,又无比的凄惨可怜。
“不够,”顺和喃喃念叨着,她白皙的小手一下下轻轻的抚过耳旁的发,执起些许静静看了看说,可惜,留不住了。说罢,拿过剪子,一下一下,更狠更快的剪下去,一下桌子上就又堆满了。她说,她对她的发说,她,等不及了。她的头皮麻痛着,剪子硌手红肿了,她也不想等了……
红,到处都是红色,灯火的红,顺和眼里的红,一身的血红。剪子上一滴滴落下的是鲜红的血,她衣服上,手上,全是,头发湿漉漉的垂挂在脑后,短短的发才尺把长。发里血,发里流出来的血!血入瓶中,合着发丝,红红黑黑一团。
顺和瘦削的肩膀不住的颤动着,眼看着那心爱的发在这古怪的小瓶子里化做了浓稠的黑色物体,粘乎乎的顺着石杵慢慢滴落在瓶子里,发出一股油腻腥臊的味道。呕~!呃……顺和强忍着心痛把那不适的感觉压服下去,从胸口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绸缎口袋,对着灯光仔细摸索又看了一会,才从脖子上取下,里面竟是一颗奇怪的种子,形状如水滴,拇指大小,却是艳红如火的色泽,对着灯火看去表皮上隐隐有着如上古祭器的细细的花纹,满满的爬满整个种子,若要再仔细盯看就发现,那艳红的种子如生命似的仿若不停的努力扩展膨胀着,似马上就要裂开来的向人宣示着它的存在,充满了力量。
只见瓶中那浓稠的黑色液体正急速的转出一个无声的漩涡,那种子在里面竟浮浮沉沉,一下浮上来旋转几圈便抬起些再猛的向下沉去,就如善泳之人探入水中般坚决,瞬间发出咕嘟一声响,如喝水般,诡异的,那液体就越来越少。看着看着,她背上的冷汗就顺着脊梁滑落下来就那样昏了过去。昏迷中,仿佛觉得有东西在身上游走,慢慢的,轻轻的;一种奇异的感觉,就象在自己想象中那个人的抚摸,麻麻的,然后她觉得恶心,彻底陷入了黑暗里。
很久她又微微张开双眼,长长的睫毛半遮半蔽的盖住了半个视线,大半屋子都被掩映在阴影里,仿佛是浓雾也进来屋子里,占据了大半空间。眼前还有点微光,不是灯芯,那点点弱弱的光早不知道消逝在那个角落,连点星灰烬都不留下。
顺和静躺在地上看着一片漆黑的屋顶,倾听着四周的声响,零星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是风声?是虫草呜咽?是花语低述?听着听着,那声音也近了,温温柔柔的高低起伏,多么的动人,多令人舒坦,是他在叫我吧,是呢,也许,这就是他在梦里头叫着我呢……
顺和嘴角泛起一丝甜笑,是他啊。顺和紧紧握住了红光灿灿的种子,死命地爬起身来,得意的张狂的抬起头盯着屋顶,仿佛那可恶的钟溪兰正如鬼魅般藏身于屋顶的梁栋之间,不时就要现身作乱似的,咬牙切齿,不能放过半分,直到双眼通红。
都是为了他,我才要一次次忍受着孤独,没有他,就没有痛苦。我以为不再寂寞如斯时却又被他深深地拖进了孤独的池水。是他给我期望,而又不经意把期望化作了无望,刻入我的骨头里,刀刀致命,我病入膏肓,连他也不是我的药。
等待的时间是那样的难熬,如同鱼在干涸的网中无望的挣扎,而他,就在那网的那一边,静静看着,就让我由身至心的干枯萎靡而死。为何要这般怜惜的眼光看我,不想让我心生怨恨吗? 怕是晚了,晚了啊,我爱你的那天起,就注定我要恨你。只是,我却不愿意啊,谁要这样的恨你
我是疯了,疯了……
有的时候,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坏的愿望也不一定有坏的结果,如今连我也分辨不了,我给你们的是好开始坏的结果,还是坏的开始好的结果。
言若,我要的已经在我手中,可戏台上,还少了那人的痛苦陪衬,叫我好不懊恼。
各起心谋
对了,用力去做你们想做的,跟着那妄念走,哪管他人死活,我会帮你们——拾掇好死的那一个。
言若,从前是谁拾掇好你,让我如今好好地来将他们也拾掇拾掇!
……
“阿和”,巯正坐在榻前,房里浓烈的药香掩盖住往日的清香淡雅,“为何才好了些日子,怎就又病成这般?”
不病这样重,你,难道还会来么?顺和心里暗自苦涩。
床上深色碎花万福锦被掩映住瘦小的身体,就连那小脸也隐藏在帐子的阴影中,只有那双眼发着两点亮光,一闪一闪,充满了希冀,在一片苍白中死死盯住了巯正的脸,贪婪而急切。
“阿和,你在听吗?”良久等不到回答的巯正不由唉叹着长出一口气,只怕就要误了嫁期了。
“表哥,不必再劝我,我自己知晓的,我不会有事。”顺和仿佛咬着舌头挤出这几个字,却字字清晰。“表哥不必太放在心上,阿和自然是有分寸,只是命中福薄才这般久病。”
顺和脸上突然悲苦莫名,眼中却盈盈有光华流转着,随即又是一叹“也不知我嫁去那边又能多活几多时日……”越到话尾声音越轻,几乎不可闻的湮没在无边的寂静中,这话说的令人不由神伤,巯正也恻然无语。
良久,顺和深深呼吸一下,锦被起伏得厉害,看着巯正一脸不忍却自顾自轻笑起来,“表哥何必如此,阿和我自是有自家的命数,表哥前程远大,贵不可言,自当保重些。”
“我已看开了,若我到那边只安心夫婿儿女,定要叫那边满意,不当误了两府相交好。”
巯正一愣,直看着顺和突然间盈盈若水的姿态,一下子明媚起来的脸,双眼里流泻出无尽的清明,哪里还有病中积弱,一回神已有几分凛然之感。一瞬间,巯正仿佛觉得眼前的人竟是从不认得的,眼前清明决然的人,巯正怅然,如此是好,还是不好?巯正的不安感始终不能停歇,他只感到有快石头压着胸,沉闷的搬不去,压得他快死去。
这,已经不是那个柔柔的乖巧的阿和了,再不会与从前一般细声的叫自己表哥。就如从前的她就死去一般。巯正突然有种不舍。
表哥,最后一次吧,你躲我,我知,我不忍你在舅舅、舅母与我之间为难,你怜我到底也还有几分。表哥,我到底也不是个物件,我是人啊,于家怎能如此待我?顺和痛苦的表情一闪而过,被子里的手紧紧握住胸前衣襟,用力。仿佛借了这力气才能说出话似的,对着巯正轻轻一笑,“表哥,阿和会早日好起来的。”
“劳烦表哥今日来看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前日里我亲手摘了些花朵儿制花糕,恰好今日做下了,表哥正好尝尝。”
“阿和你还病着,不必如此费心,你好好歇着,我也不多坐了,这就去了不扰你。”
巯正正要起身,不料顺和一只手飞快从被子里伸出来紧紧握住他的衣角,“表哥,”她仰着头看着他,还是柔柔的眼神,还是那个弱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