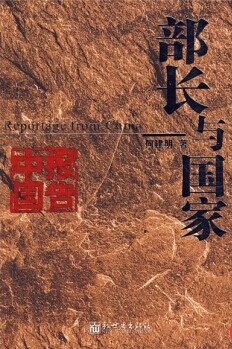祈愿者-魅步杀伐-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我娘,那伤?季祥枫一下几乎糊涂了,难怪爹那时看着自己一脸的红痕几乎气晕过去,是吗,我娘,亲娘要打死我,而我爹却为着我才逼死她?那么……娘,原是死在了我手中……呵呵,呵,季祥枫傻傻地笑开去,笑得老妇一惊,“老妈妈,是这样吗,是吗?”他问:“所以,她要走的,只因为我这样蠢!”
“可为什么?为什么?”他冲着老妇大喊着:“她还要告诉我?我是她的夫君,可她连我也不放过!”他迷蒙的双眼全是眼泪,原来他恨错了人了,可他该恨谁,他亲娘?不,她早为自己做的付了代价,他的爹?不,不……
最该恨的是那个女人,眼泪流下来,不……最可恨的仅仅是他自己,只有他自己。
他如同高烧一般不辨方向,可恨的人,蠢笨的人,可怜的人,可笑的人,原来就只有他自己而已。跌跌撞撞中他躺回了小榻,天地都在旋转,他的一切不过是个笑话,恨错了人,却还帮着她几乎灭了所有至亲,却还被她踢开去……
迷糊中他仿佛看见那人回来了,“你是谁?到底是谁?”他问,她不答,只将脸上一撕,露出那血肉模糊可见骨头的脸,她笑起来,如果那算是笑的话,然后转身就走,“你去哪?你回来!”他喊,那人停住,“我……去坟墓里……”幽幽的声音传来,“那我呢?”季祥枫听见自己问,“我——等着你,等着你嗬……”他笑起来,等着我吗——在坟墓里!
他望着那对面妆台的铜镜里自己模糊的脸,他将手抬起,剥掉了自己的所有的衣裳,他拿来那把团扇又盖在自己双腿间。他想起那只手按在那里的痛和痛快,也用手按下去,隔着那团扇的纱,他取下头上的簪子划上去,嘶,疼,可还不像那日的疼。他取来剥果子的小刀,用刀背狠狠划下去,啊!他痛得蜷起身子,然后一笔一画学着那只手,在自己身上乱划起来,刀背所到全是细细的红肿痕迹,一直延伸到脸上。他白皙的身体和如玉的脸庞如同蜘蛛盘踞着,网状的可怕印记,他看着那铜镜中的自己,笑了起来,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我不怪你,但你也等等我嗬。夫人,我该死,也想死,那——就这样死吧。
季祥枫眼中全是虚无,他抬起手腕一转,划下去,有热热的东西从他脖子里流出来,叮当,有东西掉在地上,啊!不……他听见了尖叫,还来不及含个笑容,他便跌进了深深的黑暗中,爹,来世,我必做个好儿子……
千灵寺里,烯悬侧卧在厢房里,手中的金铃一摇一晃轻轻发出悦耳的声音,上次那人掉下的,现在他也该循着来了吧。哼,她冷笑着将铃丢开,满月落进窗里,一地的冰霜。季祥枫……季相,不能怪我,我既然先许了季祥枫,要你事事不如意,那你要让他快活的过一世便是不能了。呵,祥枫,连你也没料到,季由霄最后的心愿就是要你快活的活下去吧。
如今,你可快活?她手中拿着那朵雨前兰花,叹了口气。一转身对玩儿,鸣蓝说:“先就在这里休整,后边……还没完。”
番外
路顺和
巯正表哥疯了,溪兰死了,舅母死了,全都死了,连“我”也嫁给了那季三。我醒过来所知的就是这些,一个老妇人照料着我,就在静闭着表哥的大觉寺山下的小屋里。
那一刻,我几乎要疯掉,为什么,表哥……几次几次,我都在疯癫狂乱的边沿冲向那溪水,我跳下去,用力地拍打着那溪水,却无法淹死自己,那老妇静静地看着,直到我精疲力竭,我能感到那时候表哥与我一样绝望而迷乱着心神,而他,也能感觉到我吧。表哥,我哭你可听见,你我的是连在一起的啊……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我不爱的就是你不爱的……可我还是见不着你。
溪兰是我害的吗?我那样恨她,恨不得她死去,表哥,你我的情牵扯在一块,所以她死了,死在你怀里。可我依然恨她,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我趴在溪水中,看自己人鬼不成的样子,眼泪落得无比的快。
大湘哭着来了,她服侍着我,却心不在这,她时常看着山上,有时又望着远方,她皱眉又舒展,渐渐她就不再望那山上,只陪着我却静静看着远方。后来,她说,没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了,她要回去,回去那个扮作我的奇怪女子身边,去为我求她,救救我与表哥。
再后来我等来了休书一封,我没嫁过谁,却已被休弃,可,那也表示如今我可以一心一意地等着他了,我小心地放好它,离开得远远地,等待那又一波的疯狂来临,只有那时,我才感觉得到他,就好象在身边从未离去,伸手就可及。原来这样疯去也是幸福的。
当我匍伏在溪水旁醒过来,看着自己恢复了从前的模样,一头略枯的发色,和毫无精神的脸庞,我笑起来,因为我看见溪水里那个倒影,那个古怪的女子,她来了,来收回一切。她身后的藤蔓冲进水里卷起了鱼扔进她脚下开着的黑红的花朵,我没看错,那花吃了鱼。她伸手接住几滴花心里滴落的花露,她说,这是上好的药呢,可她手一翻,那花露落尽水里。“你,想救你表哥吧?”她说,可那藤蔓却已经卷住了我,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自己向那花儿走去。
“为你对你亲娘做过的。”那女子仿佛什么都知道,我记起来,娘病重,舅舅遣人探望,春茗对我说偷听见那人道若是娘死去,便要接了我走。是呢,那个小地方人穷水恶,娘哭嚎、哀叹,病得连我也烦了。我迷惑犹豫又痛苦难耐,春茗自个去服侍我娘,我连问都懒问娘如何。不多时,娘去了,我讶异着春茗眼里那一丝得意,惊恐怀疑却不敢深问,因为,我看见了,门外飞奔过来的车马,那样的华美夺目。而她,我又怎能怪她包袱里全是未煎煮的人参,因为,那飞奔的马车尽头是一身风华的表哥啊……
我将手伸下去,闭眼前看见那女子冷冷的笑容,罢了,这是命吧,表哥,为你死也愿意……
于巯正
我知道我疯了,我也知道我做了什么。奇怪,既然是疯了却怎么那样的清楚记得一切。要是都不记得,就那样疯癫一世也许才是最好的吧。我清醒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一切声音,都在耳边荡,俗世已不是我能待下的,我跪在佛祖前,香火旺盛的佛祖却不能告诉我何去何从。“公子,定要出家么?”大师问,“大师,怎样才能洗清我一身的血腥和罪孽?”我问。
“入空门为赎罪过固然好,可,公子入空门本身却添了罪过又如何?俗世的牵挂不了,一面是在造怨果,一面却又向佛,公子,可有用么?”
“大师……”
“阿弥陀佛!公子,下山看看如何?”
我走下山,阳光刺眼,溪水的声音欢腾,而我却看见那身素衣而立的人婉约寂寞的背影,“顺和!”我听见自己那样激动,她立即转过身向我本来,我抱住她时,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表哥,我愿意的。”她也哽咽,“一只手换表哥一生,何况……那时我的孽罪之果……”
是呢,这样的顺和,我若入佛门长伴青灯,她又将如何?却果然是我的罪过,罢了罢了,顺和,我定不让你孤苦,罚我一世牵挂于你如何?我想起来和尚们手上的伤,笑起来,难怪他们也不愿留我,一个疯子,顺和,你竟然这样执着!
我们归家,拿出部分家产捐到了寺庙,春茗、溪兰、姨娘们、爹与娘,在那地底统统都再来过吧……春天,我牵着顺和空荡荡的袖子静静地走,不知道这一生要停在哪里,可只要我活着,顺和,我都跟你一起——死,也不离去。
大湘
我该知道的,那绝不是小姐,可,我的小姐在哪里?
我被那女子赶走的时候以为就是个死了,可我睁开眼,看见那里站着的不正是我的小姐,为什么,她那样憔悴,为什么,她发枯体弱,连仪态也无地坐在溪边,两眼直直望着山。我坐在她旁边,也陪着她望,巯正少爷,就在上边吧。
我服侍着她,高兴她活着,却也悲伤她这样活着,我为她梳头,可不到半刻她便疯狂地挥散了发,踢开了鞋,我拦不住她,“表哥,表哥!”小姐喊,我的眼泪流着,看见她在那溪水里疯狂地磕着头,那样的水也拦不住她碰着那冰冷的石头,血流在水里,长长地染红了溪。
“救救他,救救他啊……”小姐绝望的声音在山下回荡。我问我自己可能为少爷这样?那时,春茗对我说,只要得到他,死也就是那样,她不怕。如今,小姐为了救他,命也不要成了那样。我望着山,却怎么也无法想到曾经以为喜欢的巯正少爷身上。渐渐的我回望来路,一直一直望,我没有像小姐那样喜欢少爷,那么小姐,请让我离开,让我求她去……
我望着那玉蝴蝶耳环和三少爷的背影,心里划过的是那日的红,很红的绸缎,曾经牵在你我之间,那个眸光飞扬又骄傲无比的人,我想,我等的就是你!春茗得到巯正少爷一时死也愿意,顺和小姐没有得到却也甘心去死。祥枫,巯正少爷不属于我的,那你呢?
那主人却看懂了我,她说:“想代替我么?”我服下那药的时候 ,那样开心着,祥枫,那红绸一扯注定你我今生要在一起呢。我不后悔,不后悔,你解开我的衣,那样温柔,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要死去,可我终于懂了春茗的那种感情,不是为谁生,而是为他死也不后悔。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白天黑夜,我还是活在帐子里,我的手伸在帐子外,在祥枫的手里,他将我的手放在他喉咙上,让我的指腹轻轻抚摸那里纵横的伤痕,那一定很疼,很丑,我知道,他那样无法释怀,一次一次用刀割下去,反反复复血流成河,我听见自己一次次的尖叫,无可奈何。可我还是那样喜欢,他叫我夫人;他说,“夫人,——夫人……”我多想对他说,去找,去找到那人,可我却连相貌也无法记清,他叹,罢了,可我知道如何能罢,她在你心里早已结了个疤……
我得到了一生的奢侈应该死去,祥枫,而你与她,缘分终究没有散去,什么时候她就转过身,那时,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大湘,曾是你的——夫人!
月照王府
荷色绣牡丹纱帐轻轻被一只手撩开,一张白皙莹透瓜子脸显出一半,那睡意迷蒙全凝重了弯弯的两道柳叶眉上,唇上竟还残留着些许胭脂,带着糜艳的气息,手上通透的玉镯滑下了那凝脂一样的手臂,纱帐放下,里面的人似乎轻哼一声,立即有丫鬟上前来张望。良久不见帐子里的动静,丫鬟才下去。
“真闷啊……”帐子里传出一声叹息 。
庭院里下了小雪,一个宫装女子,在小丫鬟一把红扇的遮盖下缓缓地从穿过花丛而来,嫣红的石榴色葵锦彩织罗裙下隐隐可见镶嵌珍珠绣功繁复的绣鞋一步一点,身上穿着的宝蓝织金大披风微微擦着地面而过,远处看去身姿摇荡,美不可收的娇弱,配着那雪更兼诗情画意。
有丫鬟迎出来,接过了披风,为那女子扫了扫些许雪花,将她扶了进去。那女子直直往内房里走去,一股暖香扑鼻,温热了女子全身,层层的帷帐被素手撩起,又在她身后晃荡,她终于到了床前,不由得回望这屋子,奢华舒适,唉,她叹一声,接着立刻道:“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