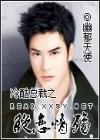血嫁之绝色妖妃-第2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素衣女子点头“这次真的是多亏了谢大哥你收留我们,否则我哥哥必死无疑了!”
“哪里,哪里!”谢泉不好意思地干笑两声,然后拍了拍脏脏的手,去了里屋。
素衣女子看着他走远,又见天色快到正午,就也去屋檐下的盆架上抱下一个晒了菜杆的木盆,想去厨房烧午膳。
突然,那堆谢泉刚刚理完的货堆里,又赫然出现一张熟悉的白纸。
素衣女子原地站了许久,终于还是放下手中木盆,走过去捡起,摊开。
一行行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从头到尾看完后,将那团纸揉了又揉,素衣女子终于还是把它塞进了腰封里,端起木盆,去了厨房。
。。。。。。
炊烟袅袅,简单的两菜一汤端上了简陋的木桌。
素衣女子另端起一碗熬得稀稀的清粥,给躺在榻上的灰衣男子慢慢喂了下去,又掀开上袍看了看他腰上已然结痂的伤口后,翻身回到木桌前,拿起碗筷默默吃了起来。
谢泉虽然一直坐在桌前,但也是等着素衣女子坐下以后,才一齐动了碗筷。
素衣女子默默吃着,不时抬眼看向谢泉,欲言又止。
吃了两口以后,谢全开始聊天地说起这几日在外面跑着卖东西时听到的看到的一些事情,突然他就提起了北越皇帝越君行在北英山被秦陌害死害和皇后南意欢失踪下落不明的事。
素衣女子捧着碗筷的手顿僵,她控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谢全愣了愣,随后还是把刚才说的话,和这几日在外面听到的关于北英山一战的事情重复说了遍。
素衣女子觉得胸口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所压,微有呼吸困难,半天说不出话来。
“颜姑娘,你怎么了?”谢全微微站起,倾了身体探来问道。
------题外话------
卡了两天文,居然卡在楚苏这里了!
过去两天对着电脑码不出来字,所以只能有15点,但是有小包子了~能饶过我不~
☆、第210章 我是楚苏,但不是西延皇后
察觉到谢全眼中微微不解的神色,素衣女子收回略略失神的视线,垂眸道“没什么。就是以前听过北越南皇后的事,觉得她没了亲人也没了国家,好不容易碰到君帝那样对她情深意重的人,如今,却又弄得如今这样阴阳两隔,怪可怜的。”
说完后,她像是突然反应过来现在这座小山地处泽州,谢泉是南秦人,不由略尴尬地歉然道“对不起,谢大哥,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
谢泉不在意地笑笑道“没关系,如今这个世道太乱,百年前我祖爷爷是南秦人,我爹是南楚人,而我呢,做了二十二年南楚人之后,如今又成了南秦人,所以,这些朝代替换的事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也没太大关系,我们只要日子好过就行。”
素衣女子低叹道“说的正好,百姓们求的不过是一个可以安稳度日的生活,可是上位者们,却总是在为那无上的权势,你争我夺,为此不惜生灵涂炭。”
“颜姑娘,我还没问过,你是哪国人啊?”谢泉小心地问。
“我吗?”素衣女子迎上谢泉看来的目光,默然片刻后,答道“西延人!”
“西延最近也在打战!”谢泉皱眉道,说着他放下碗筷,起身就想往屋外走,口中说道“我记得在路上还拣了一张西延皇帝亲笔写的讨伐檄文,那玩意如今贴的各国到处都是。”
说着素衣女子就听得他在门外廊下翻箱倒柜起来,一边还道“咦,不在这吗?难道在路上掉了吗?”
又翻找了几下,还是未果后,他挠挠头,返身,却见素衣女子站在门边,手上拿着一张纸道“是这张吗?”
谢泉走近,凑看了两眼,眼前一亮道“对了,就是这张。外面的人都说这是你们皇帝亲笔写了以后,然后找人拓印了万份,中原各国到处发呢……嗯,听说都发到东海去了!”
素衣女子看着他眸中的亮光,突然低声道“谢大哥,这真的是你无意中从路上捡回来的吗?”
谢泉弯腰凑看的动作一僵,许久,他抬头,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嘿嘿笑道“颜姑娘,你……你都知道啦?”素衣女子嘴角无奈地撇了撇,又从袖中掏出一叠十来张纸质类似,字迹类似且张张盖有西延玉玺的布告,夏风吹来,纸张呼啦作响“你这都一连拣了十来张了,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捡回一张夹在显眼的地方让我看见,我要是再不知道,再以为是大风从天上刮下来的,我就是瞎子了!”
“你……你真的是……那布告上写的西延皇后……楚苏吗?”谢泉吞咽着口水问道。
素衣女子眸色微暗,眉宇间略有忧伤地道“我是楚苏,但不是西延皇后!”
“怎么会呢?”谢泉惊讶着,过楚苏手上的布告,翻看着诧道“这上面明明写着说楚苏是西延皇后啊,你既然是楚苏,又怎么会不是西延皇后呢?”
“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你……”
楚苏无奈一笑,低声道“谢大哥,谢谢你,你应该很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谢泉面上一红,嗫喏着道“我那日出山去集市,看到满大街都能看到西延贴的这个找人布告,我好奇就去看了一眼,上面说西延皇后和她的侍卫失足掉下了断谷,虽然我是在离那断谷三十里外救的你,但我还是觉得,可能是你们俩,所以我就把这张飘落到我脚下的布告带回了家……然后我就见你对着这张纸发呆!那时候,我就想着那个人应该是你没错了。”
“你就没想过去跟官府说吗?他们一定会给你丰厚的礼金的,会足够你一辈子不愁吃喝,不用再这么穷困辛苦。”楚苏道。
谢泉摇摇头“当然没有,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也知道分人好坏。我知道颜姑娘你不是坏人,既然你看到了他们找你的告示,都没有反应,我就想着,估计你也……不太想回去……正好颜兄弟伤那么重,所以我也就没提。”
“后来我每次外出,都会遇到西延贴出来新的告示,每一封都是跟你有关的,本来看你不愿回去,我也就不打算再捡那个回来了,可是那个告示发的太多,不管我走到哪都能看到……而且每一封都言辞恳切,看着我这个大男人都觉得感动,所以我就……没忍住,就又拣了回来。”
“我就想着,我只是把它们都捡回来,也反正回不回去决定权在你,然后就一直到了今天你刚看到的那一封,我这次一出门,就看见上面写说西延国内打战了,说是什么月落部的郡主害死了你,然后西延皇帝一怒之下就杀死了那个郡主……然后,他们就开始为你打架了。”
“所以你今天回来也不是因为你的东西卖不掉,而是看到这张纸,想提前拿回来给我看的吧。”楚苏面容微微泛白,低声道。
谢泉被说中心事,却又看不分明垂首的楚苏面上神色,微有些慌乱地道“颜姑娘……啊不,楚姑娘,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你应该知道,所以我才回来的……还有就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战,确实东西不好卖,我在城里转了两圈也没有卖出去东西,所以我才回来的。”
“楚姑娘,你不会生气吧?”边说话,谢泉边拿眼忐忑难安地偷看着楚苏。
楚苏抬首,温婉一笑道“我怎么会生气呢。谢大哥你先是救了我们,然后又这般处处为我着想,我怎会生你的气。我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所以心里有些烦乱而已。”
“那就好,那就好!”谢泉松了口气,问道“楚姑娘,你真是被那个什么月落的郡主给推下来的吗?”
“嗯!”楚苏点点承认。
“那颜兄弟是你的……?”
“他是西延皇帝派来护我的人。”
谢泉望了望躺在榻上的燕杀“那你……是不是和西延皇帝有什么误会啊,不然怎么你都说自己不是皇后?可他却又派人一路护你,还这么大阵仗地找你。”
楚苏沉默,清澈眼瞳中一抹复杂,转瞬即逝。
谢泉见状连忙摆手摇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多嘴了,多嘴了,楚苏姑娘你这样做自然有你自己的苦衷,我不说了,也不问了。总之,我谢泉虽然没什么见识,但也不是那种出卖朋友换银子的人,所以你就在我这安心住下吧,等到颜兄弟他彻底好了,能动弹了,你们想离开时再离开吧。”
“等他醒了我就走不了了。”楚苏叹道。
“什么?”谢泉狐疑地又看了看榻上的燕杀。
“燕杀是他的人,所以若是他醒了,手脚能动了,肯定会要带我回去,即便我不肯回去,那么他也肯定会知道我还没死了。”楚苏解释道。
“可你不是说他这几日已经醒过了吗?”谢泉更糊涂了。
“是醒了,不过我给他的药里加了一点安神的药草,让他一直睡着的。”
“怪不得,我说既然那治狼毒的药草那么有效,怎么燕兄弟到现在还没醒,敢情原来是你…咳咳咳!”谢泉不好意思地轻咳了几声。
楚苏看着他那原本厚实的脸面上又红了些,也不在意,只问道“你那日说那治狼毒的药是从村中老者那里求来的,那他会不会也知道了我们的事?”
“当然不会,我既然猜到了你的身份,又怎么会那么笨的想不到这点呢。”谢泉扬眉笑道“我那天啊,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随便找了个小医馆,让人给我的胳膊上包扎了下,然后装着可怜的样子,去求的。所以孙老还以为是我不小心路过那,被狼给药了一口呢。”
楚苏垂眸一笑,道“还是谢大哥想的周到。”
“嘿,嘿嘿!”谢泉郝然笑了笑,道“你还是别喊我谢大哥了,听的我都怪不好意思的,虽然你说自己不是西延皇后,但总归布告上是那么写的,你这么喊我,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了!”
“那难不成喊你谢大叔,可以吗?”楚苏笑着反问。
“啊……大叔?”谢泉忙不迭道“那还是不要了,我痴长你几岁,那就还是喊大哥好了,反正我也不会喊你皇后娘娘,那就依然还是姑娘--燕姑娘好了。就当我们今天,刚才的那些对话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就依旧还是那个被我救下的燕姑娘好了。”
“如此甚好!”楚苏道。
“嗬嗬!”谢泉轻吁了一口气,没了这个秘密在心底,顿时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
这个时候,榻上的燕杀忽然低低地发出了一句咕哝声。
屋里的两人瞬时回头,奔向床边查探,幸好,燕杀只是睡梦中发出的无意识的声音,整个人旋即又沉沉睡去了。
“他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直给他喂安神的药吧?服多了总会对神智有些影响的。”谢泉皱眉道。
楚苏给燕杀掖了掖被角,默声道“我自然知道那并非是长久之计,本来我想着与你之间话未说透,诸事并不好办,可如今既然你已知晓一切,那么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今夜的稀粥里,我已经停了他安神的药了,明日一早他便会醒来,在他醒来之前我会先行离开,然后你便告诉他,在山崖狼谷里,只救了他一人吧。”
“明日就走吗?”谢泉闻言惊了惊,又道“这样说,他会相信吗?”
楚苏往窗边走两步,遥望着漆黑天幕下的繁星点点,黯声道“信与不信,反正我在他心目中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即便是有过一丝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