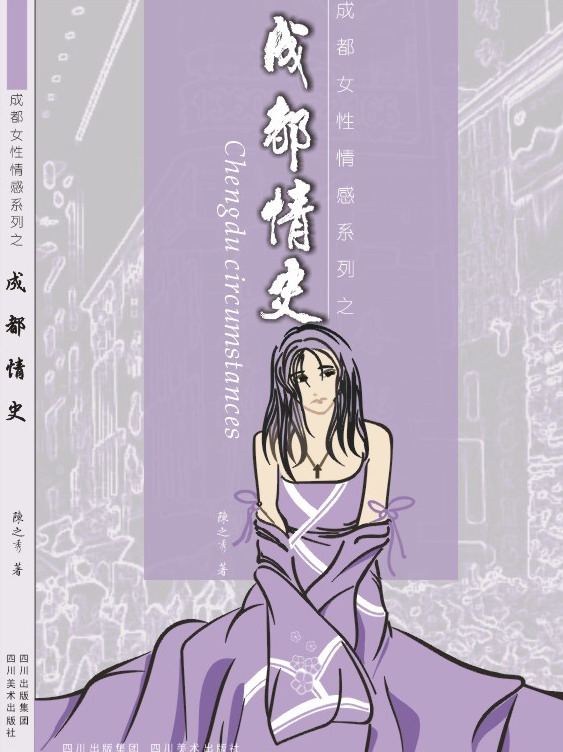成都粉子-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饭后又是唱OK,我们走出酒店,灯火迷离的夜色中,“小沈秋”看起来美得让人惊心动魄。
几步路就到了好迪量贩歌城。进了豪包,两个女人卡拉了一个来回,陈局长唱起了高亢的革命男高音《打靶归来》,唱得来左腔左调,但刘至诚激动地站起来,拼命鼓掌还嫌不足,搂着“小沈秋”跳起了不伦不类的快四步,林未晏也站了起来,我只好搂着她跳起了两步。
在刘至诚有力的带动下,“小沈秋”舞步飞旋,短裙下,两条丰润洁白的大腿如粉雕玉琢,让男人们产生一种想抱着它们地老天荒的冲动。
必须感谢这个新时代,被“肯德鸡”喂大的少女们,显然比当年的沈秋更加健美,我想下一曲,我一定要搂着她温柔地沙一沙慢舞。
机会终于来了,陈局长意犹未尽地吼完《打靶归来》,现在轮到林未晏唱《如果云知道》。
重新坐下后,我突然发现,风向完全变了,“小沈秋”一臀坐在陈局长身边。我请她跳舞,她说太累了不想跳,小鸡依人一般温柔地靠在陈局长身旁。
更可恶的是,陈局长一脸淫笑地看着她,一只肥手已经放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正往大腿根部慢慢移动,这时,林未晏深情的女中音地吼出一句:“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云也不知道!
我看了看刘至诚,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
我马上明白过来,何必云知道,我一晚上的好心情,已经从云端一直掉进了下水道。此时,我的心情和周家梅去年提出分手时还不完全一样,除了绝望之外,我还有些愤愤不平。
我提前告退,握了握陈局长的肥手,然后行尸走肉一般走出了歌厅。
刘至诚把我送到包间门口,他紧紧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人在江湖。”
“我理解。”
“这小婊子的确有点像沈秋,我也舍不得,刚才一坨钱就把她搞掂。”刘至诚说。
“以事业为重。”
“也为我们‘诚东文化’的事业。”刘至诚补充说。
看着刘至诚深情的眼睛,我欲言又止。
“不必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刘至诚的两眼已湿润。
这就叫情谊,这才是兄弟,我感动得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当然能够理解,刘至诚一定比我更喜欢这个“小沈秋”,记得他发财以前就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和沈秋共眠一宿,但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丢出这一万块钱,却把一个到手的鲜嫩妹妹,送到了一个胖得可耻的中年男人的床上。
第二天,刘至诚打来电话。
他说昨天晚上陈局长玩得很开心,这“小沈秋”年纪不大,性方面却很放得开,吹拉弹唱样样会,把陈局长“咀”得来心花怒放。
“这小婆娘这么懂事,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要操她必须抓紧时间挣钱,我下周先打二万块钱到帐上。”
刘至诚在电话里说。
放下电话,我对刘至诚的义气充满感激。不过,更应该感谢的是婷婷,虽然昨晚发生的事她会一直蒙在鼓里。
这次“糖酒会”,公司策划的“丑女”活动虽没有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但毕竟是救场如救火,婷婷算是帮了我大忙。当天晚上,我请婷婷和王建南吃火锅,我从提成里抽出五百元,封了个红包,想对婷婷表示一下。
婷婷坚决不要,我只好收了回来。
然后我问她,上次那个周末晚餐,她和王建南过得开不开心,婷婷的脸马上就红了。
她和王建南一样,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其它的什么也不说,让我觉得很是奇怪。
据我所知,有些男人风流快活之后,喜欢发一发余骚,向别人描述一下快活的细节,比如刚才那位陈局长就是。但大多数男人把这类事看得比较平常,为男女双方以后的风流事积点口德,比如我就是。但王建南更另类,对性方面的事从事不提。
以前我也追问过他,和沈秋第一夜是在什么时候,他当时特别愤怒,五官完全变形,说话音调都变了:“你问这些干啥子?已经有那么多男人上过她,你还要过问她的隐私!”
其实长期以来,王建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扮演着一个相当忧伤的爱情骑士形像。据我观察,他的失恋经历不仅悲惨之至,而且匪夷所思,惊心动魄,让任何一个编小说的人都目瞪口呆:上次林未晏的事当然不必说了,我估计刚认识她的时候,王建南一定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上个月我和刘至诚吃饭时,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把林未晏“先煎后睡”之后,林未晏一边洗澡,一边很嘲讽地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王建南,她说王建南简直是个瓜娃子,居然送一本诗集给她,上面还有他的题字:“送林未晏小姐看着玩。”
的确太瓜了,刚认识一个不错的粉子就暴露出自己最弱势的一面。
更匪夷所思的去年有一回:当时王建南频频和一个卖笔记本电脑的美女约会,一天,我们一起吃晚饭时,我问他搞掂没有,他说快了,今天晚些时候再约。这时他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后他说:呵你打错了。然后说是一个陌生女人用很娇柔的声音说:陈总啊,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唱歌吗?我对王建南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说不定是粉子。王建南想了一下,回拨过去说:你找陈总啊,我是他弟弟陈刚,要不我请你唱歌吧?对方马上同意,约好在假日饭店门口见。电话里双方说好了各自特征,王建南拿一份商报,女人说她穿一件紫色长裙。
艳遇来了挡都挡不住!王建南那天确实很兴奋。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昨晚的悲惨“艳遇”告诉了我:他等了半小时,还不见粉子出现,这时,那位卖电脑的美女打来电话,说正在“白夜酒吧”等他,他不能再等下去,马上打车去了“白夜”。在酒吧一坐下,他马上发现,美女对面坐着的女伴,穿的正是一件紫色长裙!
后来,王建南将自己的失恋经历写成文章贴在网上,以告诫世人,他的网名是“西门又吹箫”或者是“西门一再吹箫”,我的网名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深爱潘金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那些贴子,不过前两年我们上网的热情不高,像网络经济一样持续时间很短。
42
一个人一生中的艳遇是命中注定的,有多少次就只能是多少次,早晚都会到来,我经常这样安慰王建南。
拿我自己来说吧,20岁的时候我还是处男,27岁才学会手淫,28之前基本上只有周家梅一个女人,但最近两年来,上苍对我十分关怀,我大有一把将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之势。
估计到38岁的时候,当我回首往事,我不会因碌碌而为而懊悔,我把平凡的一生献给了人类的快活事业。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已经想好了,可以借用当年知青大哥最爱用的那一句口号:青春无悔。
当然最应该无悔的,是我和周家梅的初恋。
初恋时我对周家梅的第一次性骚扰非常失败,也许因为她还是处女,也许她还在犹豫,也许——我不敢去想——她爱上的可能是王建南。
周家梅在我家住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通霄没睡,第二天中午我们才起床。
桌上的水蜜桃没动过,依然和周家梅的乳房一样鲜嫩诱人,窗前的栀子花却有点蔫了,像用过的避孕套一样,开始发黄,有气无力地搭在绿枝上。
王建南已经出门,周家梅在卫生间梳洗时,我看着昨天为泡她精心准备的音乐磁带,选了一盘放进录音机,英国歌手沙黛的声音在房子里飘起来,她唱着“AS good as first time”——像第一次一样爽!
我的第一次爽吗?很难说,在认识周家梅之前,我的确有过唯一的一次性经历,我从来不敢向她提起。但这次体验对一个男人的成长来说,很重要也很幸运。
比我们高几届的大学生在他们的性成熟时期,远不如我们这一代幸运,婚前性行为自然被称为“非法同居”,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当作流氓罪判上10年有期徒刑。
当年我们的年级辅导员26岁结婚时,洞房之夜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只好像癞蛤蟆一样,蹲在新娘身上一动不动,第二天早上他说,其实结婚一点也不好玩。还有一位哥们初次和女朋友幽会,他大着胆子把手伸进了女友的内裤,马上吓得哇哇大叫,掉头就呕吐起来。
他没想到,女人那地方居然和男人一样有毛。
我的第一次却显得过于随意,缺乏准备,虽然波澜起伏,但基本上柳暗花明。
那完全出自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还可以这样说,我的第一次献给了祖国的铁路事业——成都铁路局贵阳分局的一位列车员,一个美丽的贵州女人。
在我说她美丽之后,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的确,她主要是心灵美,姿色很平常,平常得我现在已想不起她的面貌是什么模样。
这次艳遇像一个色情版的仲夏夜之梦,1989年的夏天,我登上了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我去学校补考弹性力学,这是我们专业课最难的一门,每一届的补考率高达40%,很多人为此留级,留级后正好赶上后来的“房产热”,以至于这些年来我对风起云涌的新楼盘很抱怀疑。
凌晨三点了,我还在读清华大学编的那套弹性力学教材,很快我就将知道,世界上最温柔,最美丽的“弹性”是什么。
是姚姐的乳房。姚姐是8号车箱的列车员,大约28岁,也有可能38岁,那时候我对女人的年龄没有判断力,加上又是晚上,如果有人说她48岁,我也不好意思反对。
多年以后,我一直怀念夜间的火车车厢,那幽暗的灯光、氤氲的空气总有一种令人想入非非的色情氛围,让女人们特别性感,让男人特别想放纵,当然也让小偷们想做案。
“还是清华的学生呢!”一个贵阳口音的女人。
我抬头就看见了姚姐,还有她俯下身时胸前深深的乳沟。乘客们正在昏昏欲睡,我的坐位靠近值班室。姚姐马上神色慌乱地说:“你来帮我把扣子扣起。”
我懵了10秒钟才反映过来,这是一个女人在勾引我?!顿时,佛光照顶众鸟高飞,百花盛放钟鼓齐鸣,植物交合动物叫春——难道这就爱情,难道爱情就这样降临了!
那个年代,我以为不穿裤子所干的事就叫爱情,后来知道穿着裤子其实也无关紧要,以至于后来我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了。姚姐转身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动做突然慢下来,眼神一直瞟着我,目光中的欲望勾魂摄魄,瞎子也会心中嘹亮,我一个跟斗扑爬就跟了进去——
我的确帮她扣上了胸罩的背扣,当然是在事后,姚姐的胸部很大,胸罩特别紧,我扣了好半天才扣上。该怎样描述她呢,幸好我在汶川藏羌自治县呆过大半年:她饱满的乳房像羌民家里的馒头一样硕大而有弹性,乳晕像藏民家里种的太阳花一样鲜艳。但比较可悲的是,整个过程同样也只有10秒钟,我十分惭愧,急于再度雄起。但天很快就亮了,我们必须分手。6天之后的凌晨,在重庆两路口火车站一个偏僻的公共厕所墙脚下,在姚姐野狼一般的嚎叫声中,我山呼海啸、气势如虹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姚姐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一边提上包裙,一边对我说:我们差点就把公厕的围墙整垮了。
因为姚姐的原因,在回到成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