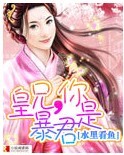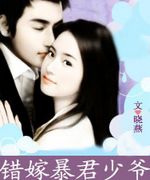暴君-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蠢,不仅仅不是救亡,更是加速灭亡。而是应该想办法和自己内心的暴君幽灵对抗,包容新事物,推崇新事物,一定要认识到只有新事物才是未来的主流,如果只抱着今天的主流不放就必然是走向悲惨的前奏。
笔者前些日子走过北京街头,偶然看见一批公益宣传画。画的是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器宇轩昂,旁边有字注释:适当上网者。 另外一个面黄肌瘦,疑为鸦片鬼,旁边有注释:过度上网者。笔者不禁摇头叹息。
虽然今天的我们没有全盘拒绝网络,但我们依然死抱不能全盘接受新事物的暴君文化遗毒。这种宣传画背后的深意则是表明我们中国还是根深蒂固地认为:目前的工业文明才是永远的主流,世界永远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比的还是这些:比的就是高速公路有多少里,每年钢产量是多少万吨,每年新建的城市有多少平方,最高的楼房是多少米;而网络这种东西不过是对主流经济,主流技术的一种补充,顶多是个辅助,而绝对不可能是未来的全部。
然而,相当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信息技术就是未来的全部。”信息化,电子化,自动化几乎会完全取代工业化,信息化高速公路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低效水泥高速公路的某些功能,甚至电子化社会都有可能会完全取代现有的工业社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依然极端守旧,或者半推半就的话,悲剧将不可避免地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发生。
早在几年前,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笔者认识好多竞技游戏高手。这些玩游戏的人都被“极端守旧”的父辈们视为“不务正业”“败家子”“二流子”……以至于后来市里面有商业公司愿意赞助并开出高薪成立职业战队依然得不到父辈的支持。最后一些高手被迫放弃理想,遵从父母的话去考了个公务员,去到乡里、镇里某个无聊而低薪的公差干干。但在他们的父辈眼里这毕竟是个“正行”,虽然一个月只有几百块收入也比一个月7、8千打游戏有“前途”。
几年后这些早期的高手们早已经变得麻木不堪,在低薪而重复的日子里结婚生子,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而一直坚持理想的“sky”等一批中国电子竞技高手们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WCG世界比赛中摘取桂冠,赢得数百万奖金。据了解目前的职业战队一般薪水都在数千不等,战绩好的战队更高达数万,更能有每年数百万的商业广告代言可拿。比起当个乡镇公务员来说可以说人家一年的收入就等于后者一辈子的收入,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而今天的人们依然对所谓的“不正统”“不传统”广为排斥。在笔者小的时候,人们都拼了命的要去当“饭碗的工人”,对“个体户”瞧不上眼。然而十几年光景,“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的下岗,破产的破产,走投无路,个体户们一跃而其认为高收入者的代表,甚至成为时代的精英。
现在,新的一批家长们不依然只顾眼前状态,把原本想从事各种职业,选择各种理想的子女们,统统逼进“金饭碗”的公务员系统。 这不难想象十几年后“下岗潮”悲剧还会重演。今天被守旧的家长们瞧不上眼的,敢于创新的“游戏高手”“网络歌手”“养猪能手”“种地新农民”等也必然会和当年的个体户一样成为未来舞台的主角。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可暴君们也总是重复上一任暴君的覆辙。生活也总是在重复,而每一代家长们又会重复上一代家长的错误。 笔者真心希望,但愿有更多的人能放弃守旧,包容创新。不要让这些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悲剧继续在下一代、下下一代人、下下下一代人身上重演重演再重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暴君的爱实排优
中国人喜欢和比自己弱小的人交朋友,西方人却只喜欢比自己强大的人交朋友。这是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比外国人过的悲苦的最大原因。
………【中】水木周平
这里的爱,是表示喜爱,排则是排斥的意思。实际上在中国集权统治下,你很难找到不排斥人才的暴君。有的史学家认为暴君排斥人才,是因为暴君嫉贤妒能。而笔者则认为恐怕并不完全恰当。因为暴君总还是需要人才的,否则偌大一个帝国难道暴君一个人就管得下来?只不过隐藏在暴君排斥非常优秀的人才表象背后的,则是暴君对老实型人才的渴望和喜欢。为了让敦厚型人才能够顶掉优秀型人才实现幻想中的“千秋万代”功臣就难免被屠戮。
其中最有名的为汉高祖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纠葛。
汉三年六月;汉军被楚军在成皋击败后,汉军东渡黄河,汉王刘邦落荒而逃。此时完全具备势力和时机夺权的韩信并没有借机落井下石,反而在刘邦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索要印信兵符时,毫不犹豫地将兵权交出,
汉五年十二月,项羽垓下之败,自刎于乌江。刘邦还至定陶时,驰入韩信军中,要夺其全部兵权。其韩信门客对韩信说:“汉王逼人至此,将军不如反了吧。”但韩信依然不反。被夺取兵权后韩信又齐王贬为楚王。
汉六年(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的计策,说天子要出外巡视会见诸侯,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韩信去陈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史记·淮阴侯列传》)免韩信死罪,贬为淮阴侯。韩信其妻劝说韩信流亡,但韩信依然拒绝。
汉十年(前197年),陈豨谋反。此时韩信手下一名被囚禁的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吕后与相国萧何商议后,由萧相国欺骗韩信入朝,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斩杀并剁成肉酱,诛灭三族。
其他历史上皇帝猛屠功臣的例子亦不少。
吴国上将伍子胥有立国之功,吴王曾要将江山赐给他一半。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但最终死于吴王之手。
秦将白起,百战百胜,平生未遇敌手,为秦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含冤而死。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历来是课本中“卧薪尝胆”的英雄典范。他起事之初依靠范蠡、文种打败了吴国,称霸诸侯。回过头来却立即对大功臣文种下毒手,赐死文种时还俏皮地说:你献了七条灭吴之计,仅用三条就灭了吴国,还有四条没用,你带到先王那里去罢。
而到个明朝则达到了巅峰,开国功臣除瘫痪在床老眼昏花的汤和外,其他全部杀光。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于自己的旗下,并放心任用自己手下的饶勇战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就开始猜忌手下的文臣武将。他耽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没有文化;耽心武将们会拥兵自重; 暗中打他皇位的主意。为使自己安心,他下了一个历代开国皇帝都没有下过的决心--就是耽心在有生之年铲除所有的开国功臣。
洪武13年,胡惟庸案发。胡惟庸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由于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被朱元章诛杀,累及三族。如果说胡惟庸一人犯罪理当诛杀,尚情由可原,但朱元璋竟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10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
洪武26年,朱元璋又因有人密报大将蓝玉居功自傲,图谋造反而不失时机地将蓝玉下狱审讯,不及诛杀,并又连累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此外,徐达食了他赐的蒸鹅后死去;傅友德被逼自杀身亡;廖永忠被诬偷穿龙袍而死于狱中,冯胜被赐酒后死去,宋濂死于流放途中,李文忠也因礼贤下士而被毒死。
在短短的18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功臣*一一除掉。其中仅有两人不是他亲子下刀,一是刘基(伯温),因为他在爱刀之前就被胡惟庸害死的;二是汤和。他当初曾和朱元璋同村放牛,当徐达死时,汤和看出了老伙伴想解除宿将兵权的心思,主动告老还乡,甚讨朱元璋欢心,重金以资,侥幸老死故乡。
……
然而历史始终是历史,政治从来都是与道德无关的,如果细细查阅各种不同的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杀不杀功臣和削不削藩一样。你即可以说是“尾大必不掉”“藩强就必反。”找出无数功臣篡位的例子来,也可以找出很多皇帝与功臣、藩王相安无事几代人的典故。
中国历来研究史学的强硬派观点都认为,藩王和功臣是必反之。即便他们本身不反但重兵和经济大权外流必然威胁中央,他的子孙后代也难免不反。史学界的保守派则认为至多只需要“杯酒释兵权”即可,杀自己的手足兄弟,杀自己的功臣绝对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强硬派或者保守派的观点其实都各有道理。本章也无意要研究出究竟杀功臣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而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本源。看看这种根源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
说到底中国的历代文化中都是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的。在封建金字塔权力结构的社会里,皇权当然是其中的至高点。 封建君王为了维护自己权力和地位的长久性和安全性,主要依靠两种手段:一就是道德礼教,二就是任用中庸之才。
第一种手段,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曾经提到过,那就是国家武力来维持:“家中夫为上,国中君为上的道德契约。”即:在家里老子犯法儿子也不能管,只能用官来管,同理皇帝犯法也轮不到臣来管,而是只能由上天来管。否则儿子就是大逆不道之罪,是要抓起来凌迟处死的,而大臣要是谋反那也同样会遭天下人反对。(比如曹操,夺权后直到他死都没敢称帝,一直都是称曹丞相。)可见这种道德不平等契约威力是足够巨大的。然而对于保卫皇权来说,仅仅依靠这个有时候还远远不够。
皇帝心理比谁都清楚,历史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更比谁都清楚“成王败寇”的道理,而舆论的倒向永远都掌握在真正的掌权者手里。只要能拿下大权夺取天下,那其中是非还不是由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呢?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皇帝的另外一个手段了。
假设皇帝把自己评价为100分,那么他就会把他认为90分以上或者他自己有所畏惧的人全部清除出去,或者干脆屠杀掉;宰相就任用自己认为能得80分的,大臣就任用他认为能得70分的,小臣就任用能得60分的。而这套理论同样被宰相,大臣,小臣们纷纷学来用之。
于是大臣选高级部下的时候就选用自己认为比自己少20分的,选地方官员的时候就选用比自己少40分的。这样一级一级的选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轮到九品芝麻官的时候,太优秀的人反倒是当不了的,只有资质平平和容易满足的投机分子能得到这些职位,甚至很多地方县太爷比一般智商的人还要蠢得多。
这种社会结构的悲剧就在于,当每一级都比上一级要差的时候,真正优秀的,有利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