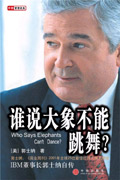跳舞的曼珠沙华-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快就是初秋了,那个时候品牌意识刚刚在这个南方城市兴起。我和蓝剑去商场的时候看见一家叫名叫“巴克利”的法国水晶店,里面的陈设美伦美涣,全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奢靡装修风格,人一踏进去,几疑走错了年代——仿佛置身在一个透明的、易破碎的梦境当中。
“这条项链很配你呢!”蓝剑指着一条蔓藤状人工水晶项链,“取下来试一试。”
我看了看标签,价值一万二,其时国内礼品店里的天然水晶也不过百十块人民币左右——做工当然差天共地。
“太漂亮啦!”乖巧的售货小姐拍着手称赞。
“但是——”我想到昂贵的价格,只好尴尬地笑笑,匆忙地取下来,还给满心期待的售货小姐。
第二天因为没有课,所以我睡到很晚,蓝剑已经上班去了,恍惚间他好像忘记什么匆匆回来取。
“是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乖,多睡一会。”蓝剑轻轻拍拍我的面颊。
不知道是不是非常安心,起身的时候已是下午,我打算找面膜来敷脸,却蓦然发现梳妆台上多了一只精美的首饰匣——迟疑地打开来看,竟就是昨天那串水晶项链。
纵然蓝剑的收入不算低,这也绝不是可以轻易得来的奢侈品。
我反复抚摩,抚着抚着竟然泪盈于睫。
(蓝剑,你知不知道水晶项链并不重要,我希翼的是你全部的爱——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想与所爱的人经营一段简单的感情,何以艰难若斯?)
水晶项链就被我湿淋淋地攥在手里,分不清是我掌心绵绵的汗,还是生将水晶捏出的汁水。
我维持着同一个姿势,不知变动,然而也就此忘记了时间——时间是什么呢?当一切归为虚无,我们还要计算什么时间?
我曾经仅仅企盼蓝剑的顾怜,可当愿望得到了满足,我却依然如此悲伤。
不知过了多久,隔壁女孩练琴的声音提醒了我,我仰起头,啊,原来已是这样的黄昏了,世界回光返照一样雍容地闪亮起来,瑰丽的晚霞以可怕而又迅捷、不容置疑的速度淹没过来,而草丛中有虫声繁密,如一场急雨。
紧接着周围传来电视剧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中年夫妻的互相埋怨、小孩不甘心的哭泣……渐渐压过了虫鸣,并不绝于耳。
人间烟火,一切都是俗世的荣辱,但和我毫无相关。
整整一个秋天,我都未从颈上取下这串项链,脚下落叶沙沙作响,胸前珠链玎铛相撞,仿佛蓝剑在我耳边的吁吁低语。
然而蓝剑与我相伴的次数却是越来越稀疏了。
我知道他非常忙,开会、做方案、争取资金……但是他总是要睡觉的吧!他夜宿在哪里呢?
我做好晚饭,默默等着他归来,等到夜色渐暗,连滚热的粥也渐渐没了热气。而他一个电话,只一声简短的“抱歉”,我便坐在屋角,一坐一个晚上,连灯也忘了开。
将近黎明的时候,远远可以看见一海疏散的渔火,我突然想起四个字“郎心如铁”。
不,我并没有抱怨、哭诉,我甚至不会稍事暗示。
这好比一首舞曲,每个人都恪守着自己的规则,我无法背离舞场的规则生生将他拉开——即使他一个月只来看我一次,我一个月也还可以见他一次。
如果思念和惶恐多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对着墙壁大哭一场,或者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然而整条街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男人,我只好又心灰意冷地回到原地。
有时候我想养一只猫,或者别的什么,只要会呼吸就好,这样,我就不会在夜深人静时,梦魇惊醒时,只听见空调机的水滴,一滴、又一滴,全打在心头上。
太清晰。
“蓝剑,你——”对着镜子我一遍又一遍喃喃自语,说着说着就忘了词。
心里头浮现出的无力与悲哀,与多年前送不出礼物的小女孩,是一色一样。
而我的性格亦愈陷孤僻,即使白日,也坐在房间里,静静等楼下的女孩子练琴。
蓝剑有时会说,屋子太空旷,不如添置些什么。
我点点头,说,好。
但是并不真去做,因为搬起家来会很麻烦,如果人常常需要搬来搬去,就不应该携带太多东西在身边。
(古代江湖漂流的人,只需随身携带一柄剑。)
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详的预感:认为和蓝剑的生活,终是当不得久的。
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定数里进入他生命的错乱算题;而我,来此一遭却只是为了他!
对着翩翩,我不是不抱愧的,但心里总残存着一丝侥幸——翩翩是流光溢彩的蝴蝶,翩翩是童话里的公主,翩翩有众多男友,翩翩夜夜笙歌……
纵使我再次牺牲了自己,也未必成全她一世的幸福。
翩翩,对你来说蓝剑不过是路过的风景,对我来说却是全部的意义——这次,我不能再让给你!
当时的我并未想到,那其实是一种纠缠,这纠缠是自桑子明起还是至蓝剑止,我却不曾得知。
这乱七八糟的命数……不可预知的结局……轮回流转的原由……层层的层层的众生因果。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相思寸灰(1)
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嗔难,有势不临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
——《四十二章经》
翩翩家的舞会延续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且不分白天夜晚,总有阵阵的音乐传来。在她的海滨花园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无数的流言蜚语、上等的香槟酒和清澈的天空下像蚊呐一样飞来飞去。
自助餐桌上永远装饰着最琳琅满目的冷盘,精心烤制的火腿和五颜六色的色拉、糕点陈列其中,没有一样不是出自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的亲自监督。柳丁和柠檬都被保证是新鲜榨出,间或还穿插各种时令水果,比如木瓜、西柚、芒果和番石榴。咖啡杯全是真正的英国骨瓷,小托盘里配合维多利亚的洛克克样式。
偶尔,我会在下午的小会客室里见到蓝星。她是个太过年轻的女孩子,神色在热情与矜持间拿不定主意。但因为行事单纯、性格可爱的缘故,总让人在某处觉得格外动心。跳舞跳累了的时候她会躺在欧式沙发上休息,风从两边的落地窗户对流而过,所有的布饰都像海洋那样溢出优美的波纹。而蓝星,就像漂流在无垠大海上的一束丁香。
我不知道她对我和蓝剑的事知道多少,但每次她看到我,或者翩翩,就露出惋惜又惭愧的神情。躲避易碎物品那般,从我们身边蹑足溜走。
翩翩是童话里永恒的女主角,她的舞鞋华丽且繁复,我有一次看见她穿着此季最流行的范思哲桃红翠绿绣花高跟鞋。
这么郑重其事的舞鞋仿佛她自身。她是在告召天下?还是叫我知难而退?只是她何苦依旧不露声色,还能继续谈笑自若?
我暗自疲惫:我们全都互不信任,但又装作亲热和谐,事情如何会演变成这般局面?
然而见蓝剑的渴望最终压倒了一切——那简直是一种毒品,我已上了瘾,并根本戒不掉!
蓝剑的脸色依旧正大光明,蓝剑的舞步仍然规矩端正。蓝剑和我隔了无数的人和音乐——无形的音乐像绵绵的丝络流苏,却也宛若森森密密的石瓦高墙——我们之间的墙,他在墙内,我不在墙中。
(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多情却被无情恼。)
但只倏忽一睐,他的眼光落在我身上,仿佛千载之前的玄月,命中注定地落在我身上。
花园里的梧桐得不到及时修剪,自然而然地浓密,并挤在一起,遮住了整个天空。有时候雨下得不大,站在下面的人几乎感觉不到雨丝,就在这个时期我遇到了戚安期。
翩翩有个女友从尼泊尔回来——那场舞会的由头就是借了她的名义。但是我直到第一场舞会结束才看见她:也不过刚刚二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厌倦与寂寞,好在相貌上的娟丽多少弥补了这一切,却偏偏穿不合时宜的粗布外套,头发掖在帽子里。
“这是紧那罗,”翩翩向我介绍,“她父亲是前驻印度使节,因此叨光在尼泊尔学了几年宗教。”
我心下奇怪:真是莫名其妙的名字,不过可能是印度名吧!这些张扬的小留学生,到哪个国家就取哪个国家的名字,反而把自己原来姓氏遮盖起来,真是孩子气的游戏。
不过若她自己快乐,也随她去——这个叫紧那罗的女子,无论是家境还是学科,和我都隔着两个世界。
九、相思寸灰(2)
我不做任何置评,客气而隔膜地点点头。
紧那罗对我也不感兴趣,只和翩翩微笑——她有着美丽的浓眉、郁气的双眼、苍白的皮肤和过分薄的嘴唇,“你大约什么时候订婚?希望我在国内的日子可以赶上你的订婚宴。”
翩翩有些尴尬,然而忽然苦笑,“订婚?早着呢!”
“哦?”紧那罗有些意外,并随手脱下帽子,那长而黑的直发有如为保洁公司代言的模特,倒是让人吓了一跳,“我以为你这次是认真的。”
“只有我认真是不够的,”翩翩自嘲地笑,有意无意转向我,“紧那罗你不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说了算的!”
她的话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字字都有深意,我别转了身。
“叶翩翩也有认命的时候?”紧那罗仰头笑了起来,用手拨了拨头发,她手指雪白纤长,耳朵像纤美的贝壳,戴一付小小的金珠,十分细巧秀气,“我以为你是战无不胜的罗摩耶那——长吁短叹太不符合你的气质!”
“罗摩耶那就不会长吁短叹?难道他不曾为悉多走失而苦痛?”翩翩乜斜了一眼紧那罗,既而感慨起来,“谁会不宿命呢?就连神猴哈努曼也有张皇失措的时候——况且爱情,更是捉摸不定,付出真心的那一方反而会十分卑微、处处隐忍……”
翩翩没说出的话飘至花间,化作一个个精灵,但随即旋成跳舞的鬼魅,张牙利爪地扑向我。
紧那罗微微一笑,不知道是因为没听懂还是格外懂。她笑的时候放荡不羁,甚至略为邪气,与秀气纤细的脸不相称。一只腕上挂满了银戒子银手镯银链子和细细碎碎的玻璃珠子,随着身体的轻微颤动,发出一连串的撞击声。
我在她们之间,局促不安又进退维谷——戒备与警惕之心都被提到不能再高,像一只猫似的,鬃毛微微扬起。
正在我左思右想,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突听远方有人招呼:“紧那罗——”
我们一起回头,却只见一位翩翩佳公子自远处分花拂柳而来,她们两个一起惊喜地尖叫:“安期?你怎么来了?”
“我又不是尼斯湖的怪兽,你们干吗那么惶恐?”他笑得十分逍遥,顿一顿又道,“人人都来得,却独见不得我来。”
“你不是移民了么?几时回来的?”翩翩亲昵地捶他,不料被他一把攥住,继而轻轻一吻手背,一本正经道,“舍不得你们呢,自然回来了!”又转向紧那罗,“这么久没见,你益发出挑得漂亮了——说吧,有多少男子为你心碎而亡?”
紧那罗被他逗得笑将起来,冰霜美人的神情立即溶化,却又流露一丝幽怨,“油嘴滑舌的劲头一点没改,我们两个月前才在斯里兰卡见过面——早忘了吧?倒有脸说这么久没见?”
只见他稍一窘,立即露出迷死人不偿命的微笑,“两个月也足够长,没听古人说;‘窈窕淑女,晤寐求之,求之不得,展转反侧’。这多亏是

![天王[跳舞]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3/3485.jpg)